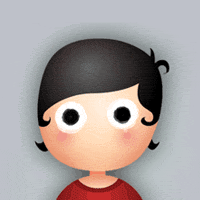宝鸡散文新地标:卢文娟
卢文娟:祖籍陕西扶风,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协理事。曾出版散文集《一莲幽香》。2014年获全国孙犁散文奖三等奖。2015年参加“陕军八0后作家培训”。2017年获全国丝绸之路青年散文大赛铜奖。作品散见于《华夏散文》《延河》《青海湖》《西安晚报》《宝鸡日报》《秦岭文学》等报刊。
宝鸡散文新地标:卢文娟
一个人的疆场
文/卢文娟
古道荒路,西风瘦驼。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跋山涉水,辗转艰辛。这一程中,曾留下张骞、班超、王玄策等杰出使者的伟大足迹。万里疆场,辉煌千年,曾吟唱在河西走廊的“三王”,岑参,高适用他们最凝练的语言和跌宕的情怀向世人展示了大漠如雪的河西风光,至今读来,依然豪情万丈,余韵徐徐。掀开历史的面纱,朦胧里看到李广利,高仙芝统帅的军队正从远处走来。广漠浩浩,来者依依,法显,玄奘,还有为国远嫁的解忧公主、细君公主、文成公主……长廊千里,英雄远去。沧桑巨变,悲歌当哭。今天,当我踩着先人的足迹,踏上这条古道,那留下数以千计的关隘遗址、故城古堡、长城烽隧、石窟寺庙、古葬墓群在我独经的疆场上伫立静候。千年已过,我来了,来聆听它为一颗存有信仰的心灵诉说着曾经的所有……
斯人已去今人在。踏上河西走廊的疆土,方可直接感受到这里最为纯净的灵魂和天空。祁连山头的积雪把纯澈的双眼映照;盘羊的心脏冲击着我的血脉奔腾不息;骆驼的双膝把我送上大漠里最美的景。《阳关曲》在梦的深处萦绕不绝,月牙泉洗涤去我三十年风月路上的尘和埃,火焰山热烈地把我所有的情爱隐藏在千佛洞的河流中日夜不绝。当我走近,唯有他在热瓦普的乐声中孤独坚守,不,这不是乐声,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始终不变的丝路情怀。瞬间,我的心被唤醒,这窄窄的河西走廊该如何安放我多年未曾停息的灵魂?
我想在一曲凉州词里把酒一杯、想在嘉峪关的城楼前横刀江湖、想在广阔的戈壁抱着自己的肉身让泪飞洒。踏上这条古道,酒成了我似曾相识的故人,端起酒,就当敬拜这条路上曾走过的所有人,英雄也好,凡人也罢,连同我所有的情一起融进酒里。麦积山石窟、雷台汉墓、伏羲庙、鸠摩羅什寺、莫高窟、嘉峪关城楼、明长城前足迹往来。而此刻,一个人站在狭长的河西走廊上,风来,响彻千年的羌笛悠然飘近,曾经和未来不容我细想。只觉一只粗糙的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我们是老乡。”我惊诧地回过头,他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脸庞上露出甜甜的笑。他告诉我,他们祖辈三代都在西域这块疆土上从事火补。西风、戈壁早已成了他们的亲人。我不知道这条苍凉的古道上有多少这样的生命?可我知道,这些火补者早已把信仰扎根在西域的疆土上,他们要给来自五湖四海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慰藉,送去丝路上暖暖的温情。
黄沙,西风连同我被炙阳烤灼的皮骨化作一丝不朽的风在一个人的疆场上广阔蔓延。我像是要和自己的身体发生一场战争的人。梦里,我驾马追寻,畅饮甘霖。我仿佛看到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的千军万马在这条荒凉的古道上正在拼杀争夺中浴血奋战!又像是看到人们在大自然降临的重重灾难中奋力挣扎。丝绸之路岂只是悠然的驼铃声和包裹在丝绸里通往西域的梦?更多的是长达千年的杀戮争夺,凄风苦雨。这从血流成河中杀出的河西长廊,从我们先辈的高贵信仰中凝结成的千年丝路。
西风漫漫,王朝更替。疆土有界,信仰无止。沙漠的明月下泛着光芒的马蹄印,沙粒滚滚,我找不到一滴不带血的沙。一个人的疆场该如何驰骋?一个人的荒漠该如何停留?丝路悠悠,奇情浩浩。当俄罗斯少年只身一人行走在西域的国土,我从他蓝色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梦,他知道在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用茶叶和丝绸换取他们的香料和珠宝。从古至今,彼此之间不只是物质的交换,那藏在深深笑容里的却是两国人对灿烂文化的共同向往与追求。少年远去,我心独存,高速公路和高铁把丝路的距离缩短,心灵的信赖和融合把丝路的文明拉近。一个人的疆场,任千万人金戈铁马。看那骆驼的膝盖里隐藏着人类最初的坚韧;那翻腾的马鬃里演绎着古人醉卧沙场的豪姿;那火焰山的河底里流淌着人类亘古不变的信仰;那如铁的驼掌上镌刻着被风雨侵蚀的不朽经文;那孤寂的热瓦普里传递着名族团结的绵绵情思。
心中的丝路通了,那连接着远方的荒滩,麦茬,藏红花逐渐远去。我像是一个孤独的旅人找到了归家的路,恍惚似梦,若一粒发白的沙土,在一大片长满红柳的戈壁上笑傲人生。西域于我,在最为隐秘和公开的地带把我深情地呼唤。大佛寺的香火、千佛洞的燕子、嘉峪关的冷风、明长城的残垣断壁……拂去尘世的喧嚣,掩不住内心的悸动。我知道,丝路在脚下,但是文化和精神的交融不只在脚下,而是在人类追求智慧和文明的心魂里。
西风漫漫,裹衣前行,一个人的疆场,世界人的精神纵横!
(此文曾获丝绸之路全国青年散文大赛铜奖)
宝鸡散文新地标:卢文娟
将文学进行到底
文/王宗仁
仿佛是一种耐心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又似乎心想事成的天遂人愿,我终于看到了在我的故乡出脱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散文作家,而且写出了那么多富有泥土质感和创意读来很亲切的文字。这就是我读卢文娟的散文真实心情。她的散文之笔触及到了她脚下这块乡土的方方面面,写亲情和乡情,她把对故乡母亲和血缘母亲的恩爱、思念融为一体,情感丰厚充盈;写自己的经历,她让个体的生命通过新生的力量在时间的隧道里得到延续;写人生边缘上的那些文字,我们能看到作者在看破浮华富贵后,表达在世俗的生活中要守住自己的本真和本然。
特别是到了这把年纪,这些年我一直总想写写故乡关中平原上那个小村庄的人和故事。默默站在村头那棵见证了乡人由穷瘠到富有的皂角村,被麦浪覆盖着的常常打湿我裤管的田埂小路,涝池岸上那座留者我瓜田时焦虑的娘娘婆庙,以及父亲肩上的铁锨和母亲拧线的纺车……越是越老,越是思念,也越发现其实自己对家乡懂得太少,很浅。即便居高临下地写点文字,总觉得浮浅,苍白。这是其一;再,就是我的精力在青藏高原那块冻土地上陷得太深,多多少少有点疏远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读了文娟那些从我的故乡长出来的散文,我心里的种子好像跌落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上,直想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树。解渴,真的!
文学最美妙的地方就是找到自身的独特个性。生活中可以进入文学的亮点,或许一眼就能发现,也可能需要投入更耐久的观察力オ行。我们常说的作家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晴就是这个道理。有了这样的眼睛才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创作。文娟的散文中给我们留下的亮点多多,那些朴实而纯美的闪光点犹如一幅幅自然的构图,乍看似很简单,细读充溢着生机又略带点神秘,好寻味。她在散文中展现的许多带着关中风土人情的乡味生活,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很幸福地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乡土上,引发我绵长的回味、深思和省悟。
这是《父亲送我去上学》里的一个场景:长途弃波到凤翔师范学校后,父亲脱鞋“蹲在座椅上,我忽然看见父亲的袜子全破了,后跟和脚指头裸露在外边。父亲好像丝毫也不在乎这些,依然和司机师傅开心地闲聊着”。也许不能用高贵来颂赞这位父亲,但正是他的“丝毫也不在乎”的坦荡,是净化我们(自然首先是文娟)灵魂的洁剂。在这位父亲面前我们会一再压低自己所谓高贵的头颅,只为抬得更高。当然我们是强忍着剧痛来看父亲的这双他丝毫也不在乎的袜子的,我们所有的奢望会在他面前一笔勾销。不要认为外面总是那么阴暗,父亲始终在我们眼前烁烁生辉。
这是作者在《书包岁月》中写自自己背着姐姐传递给她那个旧书包时的一段文字:“书书包的背后被我磨得已经发黑了,还有好几个小洞,更令人不堪入目的是,我将很多蓝色墨水和墨汁染在了书包上,那个可怜的墨绿色的书包更是“沧桑’了。好几次我背着它走在路上,一使劲不小心背带就断了。那那时候,我们的书包都是两个带子,不能往身后背只能斜挎在肩膀上。由于我经常将书包挎在右肩上,一两年下来,感觉右肩都和左肩不一样高了。最后几次带子断了,我干脆打个结就那样凑合着背。”好疼痛的回忆!不必说文娟自己了,就是读这段文字的我,这时也会摸摸自己的肩膀,我们有过同样的经历。世界就是这样,世界只能是这样。总会有人在风雨飘摇的凄苦路上日夜兼程,前方的路总是那么长,路连着天边的云,即使有风景还很远,索性不去想。我可以断然地说,就是在阳光普照大地的今天,我们也很难说就没有像20年前卢文娟背着那样书包的孩子正在上学。文娟面对自己的学生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不一般高的肩膀,她不是仅仅重温昔日的痛楚,更多的是对美好明天的期昐。
这是文娟在《人生冷暖》里记述的一件事:一个失去双脚的残疾
人,“将自己的半截身子固定在两面夹板上,板下有四个轮子,在他头
部前边的板上,搁着一个老式录音机和一个小桶。他靠着上半身的力量就这样将自己向前滑动着”。这样以乞讨为生的残疾人,我在包括京城在内的许多地方都常遇到,为什么出现在绎帐镇热热闹闹集市上的这个场景,把我的五脏六肺都搅得动荡不安!也许是那双伸在半空里无人问津的颤颤抖抖凄枯的手让我寒心?也许是那么多看热闹的路人取笑的目光使我不安?也许是文娟姐妹送到那双手里的一袋热乎乎的包子叫我感动?都是,又似乎都不是。我读出了这篇散文的内核,生活中有冷漠并不可怕,可怕的面对冷漠那种坦然处之的冷漠态度。
卢文娟的散文创作有一个明朗清晰的特点,她喜欢小处的东西,笔尖总是从很小的口子进入,寻找大的空间。一树一片林,滴水见太阳。我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写法。一个生长在乡下低处的女孩,看到的大都是些微小。她习惯守着一方小的宁静,喜欢默默地低调做人,欣赏精巧的香裙装着装。小吗?不对。正好。文学就该是写出以一当十,见十当百。我一直党得作家表现在作品中的气质一定是在生活当中养成的,写作其实都是写自己,写带有自自己气质的人和事。用文娟的话说:“大阳就是天空的微笑,而雨水就是苍天动情的眼……总喜欢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独享雨水之乐。不喜欢带伞,任雨水零落身上,雨只属于我一个人。”这女子的心境究竟有多大,我真猜不透。有了这样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胸襟,我不相信还愁收集、积累不到文学的源头!一个人的海!
毕竟,文娟还年轻,文学的路很长。所以,我要说一句话:怀终
身之忧,少一朝之患。即要常有“能力力恐慌”之心、“生活危机”之忧,才能不断地养精蓄锐,做好自己。故乡有一条世世代代人们都不知道名字的无名小河,它世世代代地浩荡着。这样就好,浩浩荡荡的歌。
将文学进行到底。文娟前路上有小小的春天!
2014年9月14日于望柳庄
(王宗仁:国家一级作家,出版作品37部,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若干篇散文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卢文娟散文延伸阅读
吃红薯的人
文/卢文娟
一、饥饿如我
饥饿如我,我如饥饿,我如农人拉着的架子车上的红薯在世人的手里被摩挲着,挑选着,我不知道自己会被谁拿起或扔下,甚至走进谁家的厨房,再进入何人的肚子。饥饿如我,我恨不得将手里的生红薯一个一个啃吃,而我分明看见那么多人坐在有着透明玻璃窗的高档饭店里正将一些精美的食物倒进了垃圾桶。
可我只是一个能吃红薯的人。路边算命先生拉着我手说:“你的前半生注定是吃红薯的命,而后半生就很难说了。”我暗自揣测,或许后半生我有吃鱿鱼鲍翅的命。而不管如何,这一半的生命我却要在吃红薯的日子里度过。
当我走过一家农户,看见一个男人端着一个大瓷碗,正吸溜着面条,那炒着土豆和胡萝卜还夹杂着蒜苗的香味沁入我心,可我依然骄傲地提着一袋子红薯招摇走过,当我回头看他,他睁大眼睛也看着我,不同的是他的嘴巴里含着没有咀嚼完的面条,而我此时,嘴里甚至整个胸腔里只有大自然的冷风和空气。
冬天来了,我更加饥饿了,可是我每天只能过活着两三根红薯的日子。这个世界上从来都很少有富人能体会一个穷人的辛酸,如一碗白菜汤,一个馒头疙瘩,半碗米饭,几根蒜苗,一棵青菜,哪怕掉在地上的半根麻花……在我看来都要弯腰捡起,因为这些都是大自然和造物主给人类最无价的馈赠,如此都是。有一天我的亲人临近病危,我没有落下酸楚的泪,而朋友却指责我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亲人病重而我却总是眼睛瞅着那些在朋友眼里分文不值的残羹剩汤。而我的朋友,你知道吗?他可是开着豪车,住着别墅的阔气之人,每天的饭菜都是十菜三汤,除了能进入肚子里的那点食物,其余的全倒进了垃圾桶,他怎么能体会到一个穷人饥肠辘辘的难过?
我梦想着一桌丰盛的饭菜。可不是吗?就连眼前剩余的半根红薯我还要留着下顿吃。地球上千千万万个富人哪里晓得,我的父亲和我甚至我的祖辈他们一直用胸膛贴着黄土地,当汗水一滴一滴浇灌着庄稼,当血泪播撒在黄土里,那些浸透了祖辈血汗的黄土地上才长出了一棵庄稼苗,经历四季的风霜雨雪,走过无数个孤独寂寞的白天黑夜,才有了那所谓的颗粒归仓。直到我拿着雪白的馒头也没有忘记这是祖辈,乃至我可亲的父亲流着血汗换来的。却不像是那些富人只需要掏出和纸张一样的钱就能买到千万个馒头。而钱在我眼中又算得了什么?怎能和我祖辈流淌的血汗相比较?
没有人知道我这会饥肠辘辘,我听到了路那边不远处有许多人欢歌笑语,而走过的瞬间,那一张张近乎麻木的面容却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旁边屋子里还有很多人形如枯木正围着麻将桌子搓洗着的光阴,那些我看不见的城市里,又有多少看似鲜活明媚的人们正在霓虹闪烁的灯影里演绎着自己人生的风霜雨雪。而我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儿,我想找到回家的路,想找到自己的妈妈,想拥有精美的食物能填饱我空空的肚子。可是除了手里拎着的这一袋子红薯,我一无所有。
二、父辈的路
如果说算卦先生说的是对的,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二十年前,我就亲眼目睹了吃红薯的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我从来没有觉得父亲是一个内心富足的人,可是从吃红薯的那一天起。
九月的风夹杂着淡凉从父亲蓬乱的头发里穿过。在沙土飞扬的渭河滩,我几乎看不见一片片翠绿的庄稼,只看见眼前的父亲佝偻着身子,一䦆头一䦆头挖下去,带着沙土的红薯像是刚落地的娃娃裸露在黄色的土地上。忽然一阵风起,漫天的沙尘遮挡住了我眺望远方的视线,我弯下身子,试图躲过这场大风。父亲说:“蹲下,将眼睛捂住。”耳边风声呼呼,我没有听到父亲的话语,只是下意识地学着父亲的样子蹲下,将头深深地埋藏在膝盖间。当狂烈的冷风卷着漫天的黄沙从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刮过,带着一个农人无奈的叹息和一个少年心高气傲的志向刮过了百亩渭河滩,刮过了滚滚渭河水。
那一刻,我睁开了眼睛,只觉得有风在耳边吼,我哭了,一个少年的泪花落在了脚下的黄土地里,我甚至觉得我只活在自己蹲着的巴掌大的黄土地上,泪花溅落,悠忽间被沙土埋没。那一刻我的心里却不曾有一丝悲伤,因为我知道多年之后,在我留下泪花的黄土地上一定能生长出一棵经受得住风浪的大树。我侧目看了看父亲,他像是风里的一尊雕塑,稳稳地蹲在黄土地上,虽然我看不见父亲的眼睛,但我相信他的眼里一定也饱涵着对这片黄土地的依爱和眷恋。
风后,父亲起身递给我一个残带着沙土的红薯,我接过来也和父亲一样的动作在裤子上蹭了蹭,看见变得光洁的红薯,我便咔嚓一口,红薯里流出了几滴奶白色的汁水,虽没多少水分,但是有种甜滋滋的劲头。而父亲吃完了一根红薯之后,继续拿起一根细长的红薯在拧了一股的草叶上蹭了几下,使劲地掰掉了红薯的两头,只剩下中间的部分。父亲带着胡须的嘴唇上下翕动着,可能是红薯的水分不太多的缘故,父亲吃了几口有些哽咽,但是脸上还是露出了一些会心的微笑,在父亲看来能有红薯吃已经很不错了,虽然比不上一碗可口的饭菜,但是在无际的荒野中,能有红薯填充肚子已经珍贵至极。父亲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我:“要嚼烂,要不红薯吃进肚子会产生胀气。”一袋烟功夫,果真应了父亲的话,我真切地感受到红薯在我胃里翻肠倒海地蠕动,可是父亲一连吃了四个红薯,他的心里又会是何等滋味?
风住了,黄沙从一处被挪到了另一处。父亲拿起锄头弓着背开始刨红薯。身后便是我装好的一袋子一袋子的红薯。九月的天也是变化多端,狂风之后太阳隐约出现,在父亲挥动锄头的刹那,我清晰地看见了父亲额头上的汗珠一粒一粒地滚落在黄土地上,或者滴落在刚出土的红薯上。我想起了几年前父亲去西山涉猎的时候遇见一位长着白胡须的老头说:“你必须在这黄土地上耕耘五十年,直到你的下一代继续接过你手里的锄头,你方才停歇。”这不是真的吗?父亲实实在在这一辈子在黄土地上,直到他将锄头交付给我,指着这一片绿油油的田地说:“你看,这是咱家的土地,地里的红薯就由你来刨。”正印证了那句话——“我是一个前半辈子靠着吃红薯过活的人。”锄头交给了我,土地就在我脚下,父亲老了,我长大了,我怎能有理由放开手里紧攥的锄头?我怎能有理由拒绝这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三、悲悯穷人
提着红薯的人恐怕比街上那些流浪在垃圾桶周遭的人富裕一些。我是这么想的。我提着一袋子红薯,至少还能吃一个星期,而那些周旋在垃圾桶周围的人除了捡拾别人扔弃的食物,他们永远没有能填饱肚子的食物,比之我是侥幸的。比起那些每天能吃鸡鸭鱼肉的生命我算不上富足,可是我的骨头里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穷苦的,反而我的目光里流淌的是对那些扔弃食物的人更多的鄙视和漠然。
我时常看见在很多条街上,那些穿着华贵的人们始终不会将半碗饭或一文钱投给那些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在一家店门口,一个踩着高跟鞋的女人摇晃着满头方便面一样的长发,涂着猩红的嘴唇,正端着一盘子炒面摇摆着走了出来,三五步哗啦一下将盘里的炒面倒进了垃圾桶,而垃圾桶背后那个他正眼巴巴地奢望着那一盘已进入垃圾桶的炒面,在高跟鞋转身的瞬间,我从她呆若死鱼的目光里知道这个女人早已经死了。不,不只是这个女人,而是千千万万个穿着时尚,满面涂粉的女人看似光彩地活着,其实已经过早地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连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已麻木、腐朽。甚至她们的骨头这会正在被自己的孩子践踏着,而这些女人从来不会感觉到疼痛,是的,死人怎么会有感觉呢?
我本自不是富足之人,只提了一袋子红薯,我能有什么去给那些可怜人呢?我开始奔跑,我记起了家里的桌上还有一些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的面包,打开门,我放下红薯,迅速地将面包装进了袋子,急匆匆地走出家门,将食物递给了那个还在垃圾桶边周旋的可怜人。他接过食物,眼睛像是一个太阳将全部的温暖和光芒聚焦在我一个人身上,即刻低下头迫不及待地打开袋子,拿出那块泛黄的面包哗啦呼啦地吃了起来。虽然他有着脏兮兮的手和蓬乱的长发,还有那件经年不换的衣衫,可是他也是需要食物填饱肚子的。在我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面包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我也正咽着唾沫,因为我一天没吃食物了,可是我的饥饿是在内心深处,不过这会看见他能饱餐一顿,我的心却知足欣慰。
回到家里,我做好红薯,一口气吃了两根,最后一根下肚的时候,红薯噎得我无法喘息,险些送了性命。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村里一位大爷着急地吃了好几根刚出锅的红薯,没过半个小时,老人断气了,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老人吃红薯太过着急在腹腔内产生大量气体。想起这位老人,我心里为那么多和他一样死在食物上的人们伤心,也为自己差点送了性命而悲痛。若不是老人饥饿,若不是急切地想填饱空空的肚子,他一定会心身悠闲地吃红薯。
生命是何等宝贵,这个世上,却有多少人正享受着眼前的食物,而忘记了食物从何而来,忘记在另一个角落还有千千万万个被饥饿折磨的人们。我,只是一个吃红薯的人,他却是一个周旋在垃圾桶边的人,而你或许是一个每天有着丰盛三餐的贵人,而来到人间的那一刻,我们都不曾带来一线一丝,之初的悲悯和善良却植种在每个生命个体里。我没有能耐去帮助太多的穷苦人,可我却多么希望那些被食物包裹的人们能悲悯自己的同胞,因为活着,我们都是人类,都是亲人。给我的我将全部拒绝,好歹我有红薯吃,已足够。足够。
四、都是安顿
我将没吃完的红薯储存在地窖里,地窖里一片漆黑,揭开顶棚时只看见一点光透了进来,我将草杆结成的席子盖在红薯上,希望它能和我一样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来年春天,我依然能吃到金灿灿的红薯。在扶着梯子往出爬的时候,我再次回头,那一堆红薯孤寂地躺在黑漆漆的地窖里,在我盖上顶棚的刹那,这里将没有一丝光,没有一丝声响,红薯是否想过,这里是我给它最好的安顿。
我盖了地窖的顶棚,顺着小路走过,一棵树落光了叶子安静地站在路边,多少年了,它怎么一直偏歪着身子,没想到我真实地目睹了它生命的最后一刻,一些伐木的人将锯子卡在它身上,在几袋烟的功夫里,它变成了几根木段。树不能长成参天大树,自然会被人砍掉,这便是对树最好的安顿。而人呢,若是灵魂里没有了真善美,又该如何被安顿呢?我想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很多东西都是上天安顿的。就如我从土地里来,终归会回到了土地里。看着蝴蝶在空中飞,它生来就是长了翅膀能飞的,鸟是不能去大海里的,鸟从出生的那天起,它就生了一对轻薄的翅膀,终归有一天会飞上天,哪怕是地上的一条虫子。而人呢,万物之长的人从生来就长着一颗充满爱的心,一个会思考的大脑,一双灵动的手。可是我们似乎在忙忙碌碌的前进中,忘记了它们的本能,甚至忘记了从一开始自己就在地上,而试图着和天上的小鸟一样飞在高空,徒劳命悬一线,却说造物弄人,其不然是将最好的安顿打破而已。
在经过几家门店时,我被一个卖红薯的女人吸引了,她被冷风吹得发干的脸庞,加上长短不齐的刘海在风里飘动,她的脖子几乎被围巾罩住,身上还穿着一个浅蓝色的罩衣。当她将烤好的红薯从火炉里取出时,有一股香甜的红薯味飘溢空中,她焦急地看着路边来往的行人,她心里期待走过的人们都能看见她手边刚出炉的红薯,前面有两个老人买了她一些红薯。她在冷风里,在红薯飘香的空气里给人家称好红薯,并收了相应的钱。我知道红薯应该是老人比较喜欢的,而我一个年轻人,也及其喜欢红薯,没有人知道我将自己的红薯安顿在地窖里,这会也拿着钱来到街上买红薯吃。她挑了一个顶大的红薯放在盘子里称好,我将四块钱放进了她的手里。她的手是粗糙红肿的,满是纹路的手臂有种瑟瑟的感觉,就连指甲盖也是褐色的。可是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路上我没有吃掉这个红薯,当我提着红薯走了很远的路,却发觉身后一直跟着两条狗,我回头,狗只是巴巴地看着我,我猜它们应该是看中了我手中的红薯,我多么想对狗说:“我也只是一个能吃红薯的人,我的命就如此,你们应该追着那些能吃到大鱼大肉的人们,追我一个吃红薯的人做什么?”一个红薯连我肚子都吃不饱,还有身后这两只狗。我索性打开袋子,掰开红薯的瞬间,金灿灿的红薯瓤夹着香味在我和两只狗之间的空气里盘旋,吐着舌头的狗明亮的眼睛看着我,也许它们知道我不是富人,却觉察到我是一个愿意将手里食物和每个生物分享的人,我吃了几口红薯,便将两端分开扔给了两条狗,它们哗地吞下了还没来得及在大地上躺好的红薯,再次看着我这个手里没有了红薯空落落的人,便依旧目光里含有温情,直到转身远去。我说过了,我没了红薯连狗都不会追我了,我还有什么资格去将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别人。
而这就是所谓那个算卦的人给我最好的安顿吗?我这个前半生只能吃红薯的人,即使有了好的食物也要送给别人。
(此文原刊载于《延河》2016年第8期)
宝鸡市职工作家协会第二届主席团
名誉主席:吕向阳
艺术顾问:权雅宁、张湛林、宁可
主
副 主 席:秦 舟 宋天泉 谢红江 牟小兵 荒原子
汉邦牛 李喜林 柏相 寇明虎
秘 书 长:麻
关注并置顶宝鸡文学新地标
就能收到宝鸡市职工作家协会最新文学动态
与其在别处仰望 不如在这里并肩
请长按图标关注
宝鸡市职工作家协会微信平台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