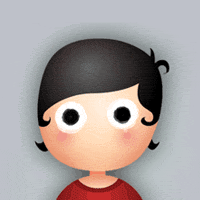我怀念油饼儿,上中学时每天啃着油饼儿大火烧穿过琉璃厂,久而久之,一路老店铺的几十块牌匾谁写的、叫什么,都门儿清。中学五年,每年200个来回儿算下来也得走了有千把趟。所以,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一提起荣宝斋、海王邨、四宝堂和戴月轩,我就想起油饼儿,并好似有一缕几十年前油饼儿的香味儿飘渺于前。
每个孩子都同样在上学的路上走过无数趟,只是他们走的不是中外闻名的琉璃厂、目力所及的不是那几十块名人书迹和无数隔窗相望的文玩古董,经过工厂或街市的孩子唤回的记忆也许是机器的隆响或腐菜和鱼腥,想起的早点兴许是茶鸡蛋或小笼包,却不一定是北京的油饼儿……
马三立曾说,“要是有了钱,我,我就吃——吃油饼儿!”这话虽然诙谐,却足见油饼儿是他那个年代的好吃的。
北京的名小吃、北京人的看家早点,油饼儿油条烧饼豆浆并没绝种,但是,它们当年的那种香味儿,绝迹了。
其实从我们过去的生活在记忆中渐渐远去、在不断淡忘中绝迹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把他们从追忆中拣拾回来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儿。比如儿时住过的房子,从进门开始沿着一侧墙壁用记忆的手指去触摸桌子椅子、书架衣柜、收音机、睡床;拉开柜门、翻动抽屉;马蹄表、照相簿、弹弓子,你日记本里的两毛钱纸币和你第一封情书的底稿……,随着记忆的展开,你逝去的老人、你争宠的兄弟、你莫逆的玩伴都会微笑着依稀映现,阳光、月亮、断墙上的树影婆娑,甚或厕所搁板上的涂鸦和短句。
所有你能想起的一切——美好的和苦涩的,都仿佛蒙着一层薄雾而发黄变淡,绝然没有当下你眼前周遭的绚丽色彩和金属质感,你今天想的更多的一切:或车或房、或妻儿朋友、或发展大计,都会使发黄变淡的过往更无足轻重。但是,当你下一次再尽力来重温旧忆的时候,你依然会感到亲切,包括你儿时的某些隐痛都可能裹上一层温柔,从而让你嘴角上翘微微摇下头。
——所以,马三立吃油饼儿的愿望才显得有趣。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当你开始回忆了,说明你已经老了。年轻人永远想未来。
——年轻人永远想未来。是啊,那是因为永远有年轻人,却不等于人永远会年轻。年轻人可回忆的东西不多,那是因为他们年轻;年轻人永远想未来,那是因为他们还有许多未来 ——虽然未来不是无限的。
驰名中外的琉璃厂,早已经不是“琉璃厂概念”中的琉璃厂,《琉璃厂》、《五月槐花香》等电视剧里的琉璃厂还多少有点儿它原本的意思。然而,“琉璃厂概念”那点儿它“原本的意思”,除了作为故人的吾等还多少留有眷恋之外,更多的各方人士谁还会在意呢?就如同油饼儿,没吃过几十年前的油饼儿又怎么会觉得今天的油饼儿不香了呢?——何况今天的孩子们有麦当劳可以早餐,——更何况今天去琉璃厂上当的是金发碧眼的“八国联军”。
前年我的画廊为90岁的漫画家李滨声办画展,李滨老给观众讲那画上的风车、铁环、糖葫芦,我问他可否记得薄脆、焦圈儿、糖耳朵,老人家当然记得,旁边的年轻人却觉得不稀奇,其实他们焉知在这隔辈人之间想到的,是些同名的两种东西。去年老画家于绍文为其将要出版的《旧京百业》请我作序,我在近结尾时写到:“所谓老北京及其文化,是在它消失之后被遗老遗少追念的,有城墙时人们不觉得憋屈,拆了城墙反倒有些空落落的,如今高楼林立没了四合院儿,年轻人没感觉,老辈人想来伤怀——若让谁搬出塔楼回平房他又都一准儿不干,时代就是这般向前进步的。”
所以,说回到油饼儿,老北京人知道,变了味儿的何止油饼儿啊?连大珊栏整条街都变了!但是不知情的外地人到北京来旅游,品尝的所谓 “正宗老北京”的大餐或小吃,十之八九都是他们的“乡亲邻里”先来一步制作的。只有一件是肯定的,那就是:外国人来吃的一定是中国的。
阅读往期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