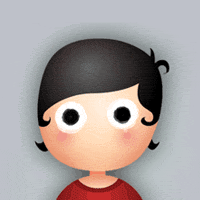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NO.235】
小召文学·人间烟火
一个关乎生活、生息、生存、生命的公众号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团火,路过的人只是看到了你的烟
端午的香味
作者:李明阳
“棕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今天的少年对端午节已不那么在意了。但在我的心里,端午节却是那么的亲近,粽子、艾叶、杏子的香味混合着母亲做的饭菜的香味,洋溢在我的梦里。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小时候,看着地里的麦子逐渐泛黄,知道端午节要来了,心里止不住噗噗地跳。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那时唱的一首《丰收歌》特别抒情,“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骄阳似火,生产队的社员们头上戴顶草帽,脖子上围条毛巾,挥镰收割,汗流如注。累了,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端起盛水的罐子,一仰头,咕噜咕噜喝上几口,擦把汗,接着干。为赶在端午节吃上新面,大家把收割上来的麦子挑到场地上,铺开,在太阳底下曝晒。正午时分,麦子晒得焦干,社员站成两排,面对面,挥舞着连枷,你进我退、你起我落,“嘭、嘭、嘭、嘭”地打麦子。再把脱下来的麦子扬净、洗净、晒干,然后连天带夜用石磨磨。雪白的、带着香味的面粉从磨盘间汩汩地洒下,成为端午节制作点心的原料。
今天的人们不大吃油炸食品,但在缺盐少油的当年,端午节油炸点心一定要吃的,好多农村孩子说是盼过节,其实就是盼这天能放开吃点心。油菜割了,家里有些油,麦子割了,家里也有了面。一年到头孩子们难得吃上什么,这天,母亲会把面和好,用小勺子一舀,放到滚油锅里炸面点;或者把面发好、切成条、绕成女人辫子状、放在油锅里炸油条,让孩子放开量,吃个够。一大早,村子里、镇子上,到处飘着油的香味。那些接未过门媳妇回家过节的小青年,除了给“对象”买件花格子褂子什么的,有的还会提上用细竹竿串起的一挂油条呢。
讲究的人家端午是要包粽子的。老家有位卖粽子、凉粉的汪老奶奶,小脚、穿戴清爽,手脚利索。夏天在街道的屋檐下卖凉粉。一个小方桌,铺上一块白布,白布上放一块脸盆大小的凉粉,上面用干净的白纱布搭着。桌子边上放几个青瓷小盏,分别是麻油、酱油、醋、葱花、蒜茸、碎盐、青椒丝等,桌子四周放四条不高的条凳。你给上几分钱,老奶奶就用一个茶杯口大小、筛状的、有个小把的器物在圆圆的、光滑的凉粉上这么一旋,一根根细细的凉粉便从网眼窜出,老奶奶将那粉条轻轻地挪起来,放到青花小碗里,依次浇上各种佐料,这不,一碗凉凉的、酸酸的、滑滑的凉粉就端到你面前了,不急,你坐下来慢慢吃,嗞溜嗞溜的,酸酸的、麻麻的、辣嗖嗖的,只吃得满嘴香喷喷、美滋滋、凉润润的。端午节快来了,老奶奶小方桌旁边便多了一只小木桶,桶里装的是刚从深井里打上来的冰凉冰凉的水,水里浸着清凌凌的粽子。粽子不大,包得有棱有角。那时的粽子不象今天的粽子里面有馅,纯米的,用青青的粽叶包的,一解开,雪白,散发着米香和粽叶的清香,蘸些白糖,味道好极了。当时只觉着老奶奶卖的粽子好吃,到以后,读了书,才知道端午节吃粽子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知道屈原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知道屈原看到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于五月五日抱石投汨罗江身死;知道楚国百姓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好让鱼虾吃饱了不会去咬屈原的身体,这便成了后来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
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都会买一把艾叶,艾叶悬挂在自家的门头上,说是能辟邪。其实艾叶是药草,芳香、苦燥、辛辣;艾叶浴有理气血,逐寒湿,止血,安眠,温经的功效;艾叶烟薰对很多病毒和细菌都有抑制和杀伤作用,对呼吸系统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端午是个收获的季节,与麦子一道成熟的还有新鲜蔬菜,如黄瓜、瓠子、辣椒。那时的蔬菜比今天新鲜,吃的菜有的就是头天晚上甚至早上摘的,带着藤叶的青香和泥土的痕迹。菜也好吃,黄瓜是黄瓜味、辣椒是辣椒味,不像今天超市里的蔬菜,一股白水味。新上市还有杏子,装在小竹篮里卖,黄的、青的、半青半黄的都有,酸酸的、甜甜的,味道特正。我喜欢端午节母亲做的饭菜。那时家里用的还是烧草的灶,我在下面烧火,母亲在上面炒菜。母亲让我把火烧得旺旺的,母亲在锅里倒进菜油,待铁锅冒起青烟,母亲便把勾兑过豆粉的肉丝“嗤拉”一声倒进锅里,迅速放进切成丝的青椒,再放上醋、酱油、盐,立刻满屋喷香。母亲切黄瓜片又快又薄,拌起来佐料进得去,吃起来脆且有味;母亲炒的苋菜汤汁红红的,浇在饭上,雪白的饭粒也染成红色的了,软软的,特别好吃。老家的小厨房不大,有时菜的热气、饭的热气竟使小厨房里热气腾腾,热气透过小木格窗户,飘向屋外……正是:“天下奇观看尽不如书卷好,世间美味尝来无过菜根香。”
端午节也随父母喝点酒,微醺时,感觉这端午的阳光与平时比似乎更黄、更亮、更温馨、更亲昵,让人感到一种惬意的慵懒、莫名的惆怅和淡淡的伤感,而且这种少年时的感觉一直延续至今,是源自儿时对父母的依念,还是少年时爱情的萌动,是壮年时事业未成的惆怅,还是老之将至的感伤呢,一直没想清,也讲不清。前不久读到唐人殷晓藩《端午》诗,说的是:“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鬓丝日日添白头,榴锦年年照眼明;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仔细想去,似有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