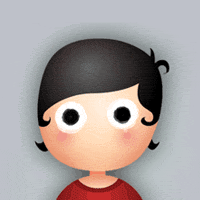热锅凉油,冒烟鼓泡,放进去的是面食,炸出来的是日子,散出来的是年味儿。
家的这种温暖和美好,不仅存在于齿间,且滴水穿石,印于心头。
今日送上豫西地坑院的风情年味儿系列之炸油食,真是一锅热油催生盼了整整一冬的好吃,丸子酥肉,麻花馓子,样样平常,样样暖心。
那么此时问题来了,为什么过年要支油锅、炸东西呢?
张冲波 | 文图
谈谈炸油食吧。
炸麻花,炸油撇头,炸油陀,炸油馓子,还有炸红薯片子,炸豆腐,炸菜丸子,炸肉丸子,炸小酥肉,而用的油是,棉籽油,菜籽油,还有大油,羊油,等等。
炸油食,一般在腊月二十五,和面,盘面,醒面,切面,最后下锅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麦子,自家淘水晾晒,连夜挂号排队,在生产队磨子磨面。
乡间木匠自制的升降磨子,麦子被高速运转的磨棍子挤压粉碎后,经倾斜的传送带抖动,细面通过密织的网眼漏下,这是第一茬面,最白最亮,被主人收起来,将来蒸出的馍雪白,擀出的面有筋道。
这一茬面,约占四分之一。剩余的从筛眼上边溜到底仓,再用木瓢装进布袋背到上边最初进口倒下去,再一次接受磨棍子的打压,再一次通过网眼筛选,筛下去的第二茬面,颜色略带灰暗。
如此这般反复筛选,麦面就出来了。一般人家磨出的是八五面,就是一百斤麦子,磨出八十五斤面,剩余的十五斤是麸皮。
光景好的人家,麦子少磨两遍,出的是九零面,面白一点,口感好一点。
我们家穷,人口多劳力少。每逢我和父亲磨面,爷爷总是千叮咛万嘱托,“记住,磨八零面!”
所以遇吃晚饭,邻居们蹲在门前土巷子大槐树下,我老挒得远远的,怕人家说我碗里面条即少且黑。但腊月磨麦子,爷爷的口气就变了,“磨个九零面吧”。
有了纯天然的好面,自产的绿色环保食用油,加之奶奶的巧手艺,色香味俱全的炸油食就应运而生了。
先从炸油撇头说起,案板上切成巴掌大的菱形,放满一条盘,,丢进沸腾的热油锅里。
先是沉底,不多会儿就胖鼓鼓浮出油面,鼓包里的热气,寻找缝隙一丝丝冒出来,直直的。有的热气口朝下,油面的反作用力,让它翻个个,打起旋儿来。
一锅十几个这样的油撇头,左旋右转,碰碰撞撞,如一锅活蹦乱跳的小鱼。我和二弟、三弟站在锅头台前围观,小声嘀咕,指指点点,预定油锅里翻滚的油食,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
母亲一边拿两根长筷子不停翻个,生怕油淹那一面时间长了焦着,一边拿眼睛瞪我们,“吱声,不准叽叽喳喳!”
豫西乡间有忌讳,就是炸油食时不许高声说话。要不然会出现一些怪事情,要么油锅突然“溢沫”,满锅冒沫看不见正炸的油食东西。
再严重一点,溢沫带出热油,顺锅沿溢流到灶膛,火星与热油相遇后果不堪设想。要么,无论怎样添柴加火,油锅都不会滚热。这叫犯邪。
再一个,正炸油锅时,若有外人进院子,也会出现上述情况。所以,邻居走到某家院子大门口或崖上,闻到诱人的油香间或呛人的油烟,都会知趣后退。
其实,炸油食的过程,静默,小声言语,就是一种仪式感。一介小民对苍生的敬畏,对神灵的膜拜。
待第一锅油食出来,母亲拿一个粗瓷碗盛满,端到上院窑里,先敬老君爷和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再敬列祖列宗,地下有灵护佑后辈。接着才是我们兄妹几个随便吃,这可是盼了整整一冬的好吃。
我们很快吃完一大碗,起初母亲炸的油食是供应不上我们几张小嘴的。母亲不时提醒道,肚子留个空,下边的更好吃。
是的,麻餹出锅了,父亲的拿手活软面麻餹。先在案板把醒好的面团切出一块子,然后搓成圆状软面条,反复搓反复拽长。
这时截出尺半长粗条,两头对等折齐,一只手捏住这一头,另一只手捏住折弯的那一头,在案板上反复扭搓,两条扭成一根。
如此这般再扭一根,把这两根又扭在一起,搓两下,然后小心翼翼平放进油锅,很快,热油围着麻餹冒泛气泡,有灵性的麻餹越扭越紧,像一对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侣。
父亲下锅子,母亲添柴烧火,主烧玉谷芯子,她不让我插划,怕饲弄不好耽搁事。
奶奶的任务是在窑里,和面,醒面,一盆一盆的麦面,在土炕上用棉褥子捂住,发力,发软,整装待发,变着花样往油锅里跳。
麻餹是故乡一带对麻花的统称。所谓软面麻花,就是和面时稍微多兑点水,油炸出来通体软和。
而硬面麻花,和面时少兑水,面和硬一点,揉搓方法基本相同。只是体量大,硬度大,油锅炸点均匀,出锅色泽一致。
炸硬面麻花技术难度大,就连心灵手巧的父亲也望尘莫及自叹弗如。
记得小时候,要吃上硬面麻花,必须请一位叫“文”的老汉。老汉曾师从灵宝县城一老师傅,而本师傅当年给躲八国联军西逃的慈禧做过麻花,老太后赞不绝口。
文爷住在我家背后那座地坑院,不苟言谈,整天板着老脸,大概乡间有手艺的人都是这个态势?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节,或者腊月过大年,我爷爷都要请文爷来炸硬面麻花,一炸就是满满一掌盘,粗且长,香且脆,酥且硬,黄褐色的光泽,暗香浮动。
我毕恭毕敬捧在手里慢慢咀嚼,好像吃的不是麻花,而是一种口福。那时候不兴给工钱,临走时,奶奶给文爷包上十根带回去。
着重说说我的最爱——油陀。若看见油陀,我会奔她而去,舍弃一切的油食东西。油陀浸的油多,炸得到位的话,面油全浸透,简直是个油疙瘩。更确切地说,我借助面这个载体通道喝油。
饥饿年代,饥肠辘辘,面食多,油水少,肠子需要滋润,年少体弱的我下意识补充营养。
炸油陀相对复杂些,和面糊,擦萝卜丝,然后抹在油勺里,放进热油锅炸。奶奶仔细,把秋后收摘的南瓜完好无损地保存到腊月天,萝卜丝南瓜丝,少许盐,一起放进稍稠的面糊,在粗瓷盆里搅和,用锅铲子挑起,放进平底油勺,味道好极了。
油勺子圆形,直径二十公分,深度一公分,这样最合适。要不然,炸出来的油陀,稍厚或稍薄,稍窄或稍宽,视觉上都不美观。要么是个傻大饼,要么是个小家子气饼。
一般人家是普通的铝勺,而我家是上乘的铜勺,勺底油渍斑斑,勺把起明发亮,上辈人传下来的。
土改前,我家是重王村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这把铜油陀勺是唯一没有被没收的传家宝。
勺把与盛放面糊的勺底成九十度垂直角,抹好齐平勺沿的面糊后,父亲手执勺后把,小心翼翼沉入油锅,不多会儿,只见勺底周围频泛细泡,面团拥抱清油情话连连絮语不断。
这时,油陀和勺子自动分离,彻底投入油锅,在沸油和热气的簇拥下,打着旋旋,跳着回旋舞。
有时浸油的面团与铜勺底难舍难分,父亲掂起勺把出油面,拿勺底轻轻磕碰锅沿,油陀自然脱离勺子,一下子溜进滚烫的油锅,重新回到沸腾的生活。
紧接着,父亲麻利地抹好下一个油陀糊糊,把铜勺再次沉入油锅,。
趁此间隙,赶忙翻个上一个油陀,赶忙捡出上上一个油陀出锅。期间,我也自告奋勇翻捡油陀,更有甚者,直接抹面糊下油锅。
高难度动作是勺底相磕锅沿,一个是时机的选择,早磕,黏黏糊糊不分离。晚磕,焦着干粘在勺底难分离。
另一个是位置的选择,离油面近了,相磕时撞击热油四下飞溅,弄不好会上手上脸灼热灼疼。离油面远了,落差大,自由落体运动,同样热油飞溅,拿捏不好前功尽弃。
还有炸干片子,把面擀成普通面片那般厚,再切成一扎长、半扎宽的面片,然后三片同样尺寸的面片叠加起来,在正中间顺长犁开三寸半的刀口,分别把两头折进去刀口再从背面掏出来向后扯,于是平面的面片有了立体的造型。
接着小心丢进油锅,沉浮,翻个,嘶气,焦黄出锅。
干片子刚出锅不好吃,放凉后,脆,酥,香。故乡人变着花样炸油食,就是为了勾起食欲,把单调的日子,在形式上过得繁复一些。
对于油食来说,油就是色,型就是相。色相,色与相分不开。
炸罢油食,炸豆腐,炸菜丸子,炸肉丸子,炸小酥肉。粘上一些面糊,披上一层外衣,热油抵达菜蔬,抵达肉类,不那么胶着,也就不那么焦灼,菜香自然而然发挥出来。
肉香从幽闭的深处散发出来,不再浓烈的肉味,不再生涩的肉味,不再油腻的肉味,一切都是温度的提携,一切都是热油的浸润,小小油锅演绎无数人间美食,演化人生无限意趣。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冲波,河南灵宝人,豫记专栏作者。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曾任卢氏县志副总编,现供职于农行三门峡分行崤山支行。近年致力于口述史写作,采访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挖掘民间记忆。
推荐阅读
沙土里炒出来的地坑院年味儿
地坑院里的童年:铜火锅熬出美味佳肴
—END—
豫记 | 全球河南人的精神食粮
豫记QQ社群:365802781
合作电话:13503998760
投稿邮箱:yujimedia@163.com
豫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