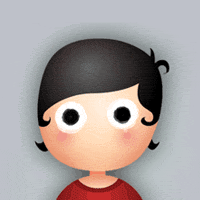北阳河从西南罗万山北穿过马安市,在市北郊区马头村边上拐了个弯儿,马安港于是便被规划在马头村附近,马安港码头距离马安市区约有三十公里,这个码头修建项目是市里刚规划的工程,由马安市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具体执行。
三轮车开起来噪音太大,二人一路无话,都在回想方才场景。大约又过了四十分钟,三轮车停在了一个撒满碎石渣的交叉口,周围一片荒凉,在东北方向有个村子。司机下车收钱,接钱的时候讪笑着说道:“刚才您二位可够厉害的,把那几个人吓成那熊样?”
老洪嘿嘿一笑,说:“那熊样,也不如你这样的解恨。”司机苦笑着脸没有说话,老洪又说:“还不是你带我们走这破路。要不你在这等会,我这兄弟来码头看看,一会可能还要回去。”见司机有些犹豫,又说:“要不你这回去可能也是跑空车嘛,能拉上他,你又赚点。”司机这才答应。
见老洪处处为自己着想,罗万山心里十分感动,这么偏僻的地方,想要临时找辆能回市里的三轮车还真不太容易。“怎么称呼你,师傅。”老洪问。
“叫我老刚吧,哦不不,大哥,你就叫我小刚吧,我不到四十岁呢。”司机憨笑起来。
“咱也才四十多嘛,这是我小老乡,罗万山。”老洪道。
此刻老洪对罗万山也已是刮目相看,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居然还有这样的能耐,于是对罗万山格外上心,心下免不了还有些拉拢的意思。
老刚看了看时间,才上午十点不到,说:“前面路更不好,但还勉强能走,你们上车吧,我带您二位过去。”
三人又沿着被渣土车压的坑洼不平的石子路向前,一直向西北走到了河边码头。
老洪说,这项目刚开工没多久,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水下打桩机进场,水底钢桶的焊接,钢筋的加工,等等都在进行中。而他自己是开打桩机工人的领班,前些天先帮老板把打桩机送到工地,这才得空回家一趟,没几天又慌忙赶回来了。
工人们见到老洪都客气的打招呼,也有人高着嗓子说:“老洪回家一趟,身子怎么没见亏,瞅着又壮实了。”工人们咧开了嘴,老洪捡起一个小石子丢过去。那人弯腰躲开,把两只手抬起,学着舞女的样子夸张把屁股一扭,又装着女人的强调,尖着嗓子道:“哎……花婶子开始烧饭等你哩。”惹得大家哈哈哈大笑。老洪笑着指了指他,没有多说,带着罗万山继续向前走,一边走一边给罗万山介绍工地情况。罗万山心里更加佩服老洪,认真的听他说话。
工人们个个灰头土脸,背脊黝黑,间或还有一块红的,那是晒退的死皮脱落后长出的新皮。工人宿舍是随便搭起来的木棚,四下里剩饭剩菜臭气熏天,红的白的塑料袋在风中哗啦啦的响,司机老刚捏着鼻子走过。罗万山对这些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里好像打翻了一只五味瓶,那种对大城市的幻想忽然破碎。原来这就是打工?
工棚下电焊机刺啦刺啦的响,罗万山看过去,眼睛一阵灼痛,立刻转过脸,看到哪里都闪着火花。那边弯钢筋的工人龇牙咧嘴,脸憋得黑红,正弯一根钢筋,生生把那手指粗的钢筋折成了圆,然后哐的一声,丢在一边,接着又弯下一根。
烧饭的花婶子已经在准备午饭了,白菜、萝卜和肥肉摆在地上几个大菜盆里。弯腰泼水的时候,透过圆领,看的见花婶子的两只大晃荡,罗万山不禁红了脸。那洗菜的水是从北阳河里挑的,很清澈,上面还飘着水草。边上的脸盆里还有几条已经翻起了肚皮的鱼,有鲢鱼和草鱼。
老洪说:“这里鱼特别多,只要得了空,俺们就用雷管去炸”。
说是雷管,其实就是在啤酒瓶里装上鞭炮火药,点上火,往水里一丢,嘭的一声,一会儿便有鱼翻出水面了。但花婶子总是嫌做鱼太费油,除了油炸,她也不会其他做法,所以大家伙一周才会有一次炸鱼吃。
看完工地已经十一点了,司机老刚开始着急,催促罗万山。罗万山心里惦记着颜美,又见工地上这番景象,也就不愿多留。老洪本来留他二人吃午饭,看他执意不肯,也就不再强求。可他担心罗万山为人老实,拉着他单独又叮嘱一番,最后告诉他,外面若待不住就到马安港找他,保证有饭吃。
告别了老洪,罗万山心中忽然有些不舍。茫茫人海,遇见的第一个人居然如此仗义和投缘,心中自然十分庆幸。
三轮车回去的时候走的是大马路,叫长河大道,是市里专门为了马安港及其周边发展而修的。宽阔的马路上,只有几辆挖掘机和渣土车跑得飞扬跋扈,到处都是灰尘,黄土和碎石撒了一路。三轮车屁股后一路喷着黑烟,突突突的跑得飞快。
到了马安市区时,已经过了吃午饭的点,罗万山和老刚早已饥肠辘辘。
“小伙子,我带你找个地方吃饭吧。”
“叫我罗万山就行了,师傅。”
“好,你就叫我老刚。前面有家牛肉面不错,咱们过去一人来一碗。”说着便开着三轮车七拐八拐的进了一个巷子,停在一个店门口,店里污水沿着车轮印正往外流。
“老板,来两大碗牛肉面。”
“好嘞!稍等啊。”
罗万山仔细的看着店里,那锅炉乌黑油亮,下面的火炭冒烟,锅里的牛肉汤香味窜进鼻子,他的肚子突然咕噜咕噜的叫个不停。
一会儿功夫,那老板就端上两碗热腾腾的牛肉面,还殷勤的搬出一台小落地扇对着二人吹,罗万山身上一阵舒坦。二人拿筷子挑起面条,一边吹一边往嘴里送,一会儿功夫,连汤带面全进了肚。
“马安大学怎么走,老刚?”罗万山看着半仰在椅子上剔牙的老刚,忽然问道。
“马安大学啊,在三和区,离这里也不远,整个马安也才方圆三四十公里。”老刚有些疑惑的打量着罗万山,接着说:“你要去?”
“嗯,想在那附近找个活干。”
“去那方便,半个小时就能到。找活嘛,估计不好弄,现在许多人都下岗了,我原先也是化肥厂的,今年年初被打发了,这才出来跑三轮养家糊口。”
“那能干点啥?”
“老板,你这还要人吗?”老刚半开玩笑的向那饭店老板道,老板也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
“哎哟,大哥,咱现在养活自己都费劲巴拉,大厂子里都雇不起人了,咱还能雇得起?”老板酸溜溜的说道。
老刚笑骂说:“这世道变了,铁饭碗都他妈的生锈了。”
老板说:“可不咋地,金饭碗也得生锈,别说是铁的了。咱邻居是干部呢,现在都说准备不干了,要自己干买卖。”
“这些人,要跟咱小老百姓抢活路,咱们就只有死路了。”老刚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他肥胖的脸因为刚吃完面的缘故,闪着油光,也变得红润起来。
“是啊,端着金碗,跟乞丐拿食!”老板愤愤不平的说。
“娘的,咱们脱了鞋追人家铁饭碗,裤子裤衩都快跑丢了,这还没撵上,人家又不干了,挪窝了,他妈的。”
罗万山越听越迷糊,云山雾罩。临走时,罗万山抢着付了二人饭钱。
老刚拍了拍肚子,打了个嗝,说:“兄弟实在,大哥今天免费送你去马安大学。”
出了小巷,老刚载着罗万山,沿着大马路一直向南。秋老虎虽然厉害,但因头一日刚下过一阵雨,碧空如洗,还是有一丝秋高气爽的味道。隔着车窗,罗万山仔细的打量着这个城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宽大的马路上,大小轿车飞奔,公交车一边冲,一边将喇叭摁的贼响,一路还有自行车铃铛声跟着一起呼应的,此起彼伏,叮叮铃铃。路边林立着许多店铺,饭馆儿、商品杂货店、服装店,街边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广告牌子挂在电线杆上,有些已经掉了框的,在风中招摇的舞动。三轮车穿过一条长长细细的老巷子,那巷子两边挤满了饭店和大排挡,客人不多,所以小店老板们抽着烟,摇着蒲扇,还有些勤快的人已经在洗碗洗菜的准备夜市。
“当心呐!”有人招呼一声,还没等人反应过来,一盆洗菜水就泼了出去。
走过这一路,罗万山才真正的见到了城市的繁华背后的杂乱。繁华的是城市,孤独的是人心,寂寞又藏在了孤独后面,越是繁花似锦,越是空虚。所以他突然觉得孤独和索然无味,这城市好像一个巨大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他甚至有点想念那满肚子坏水的俄海波和俄海涛两兄弟了。
“到啦,兄弟。”老刚吆喝了一嗓子。
“哦,这就到啦。”
“嗯,这一块我也经常跑,学生出来进去的多。”
罗万山紧张的下了车,望着学校的大门。四根约有三米高灰白的方柱撑着一扇黑色的铁门,大门紧闭着,只有右边一个小门半开半掩,有一些年轻的学生进进出出。这门正好是在对着一个丁字路口交点,门朝东。大门周边没有太多的商店,路边两排法国梧桐树,大大的叶子在风中细碎碎的舒展着,从这里向三个方向蔓延开去,平添几分静谧的味道。
“好啦,这就到了。兄弟,厂里不好进,你可以先在小饭馆里打打零工,咱们后会有期。”
“哦,好的,谢谢啦。”
“甭客气,这一块我也常来,没准咱们以后还能遇到呢。我叫张从刚,你要是真有事,也可以随便找个三轮车师傅问问,大概大家基本都知道我,跑这个没别的,就混个脸熟。”
二人客气了几句,老刚便上了三轮,突突突得骑着车便走了。
罗万山伫立在那里,心中激动万分,一路的艰辛不停的冲动着眼眶。望着那仿佛期盼已久的大门,就像是看到了颜美的背影,心中有一千一万句话想要对她倾诉,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却又忽然又想起,颜美连自己都还不认识,又该如何开口呢?但他天生有股子倔劲,且近些年的经历也让他越发的勇敢和坚定起来。
许久,他才终于踏入了马安大学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