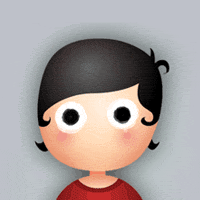金 花 高 丽
《大火磨》之风土人情原始草创稿花丛拾遗
陈村山人
二十六
鲍连长一行人马草草巡视完边境目标,匆匆地赶了回来。路过瓜地时一名年轻的勤务兵两腿夹了一下马肚子,凑上前去,向鲍连长敬了个礼:“报告,报告连长,弟兄们说这家瓜园的瓜熟了,都闻着香味儿了,请示连长,那个嘛——,要不要给太太、少爷、小姐捎带一些回去?!”
鲍庭玺嚷嚷道:“嘛?你说嘛?哥儿几个长了狗鼻子啦啊!好啊,都下来把马拴好,跑了几十里地,让弟兄们吃个稀罕。”
张家一家人围着瓜窝棚里里外外的忙活着,二媳妇凤琴风风火火地磕鱼、切肉、摘豆角,三媳妇玉珍忙着点火、和面、烙油饼。张财张富俩兄弟把预备好的旧梨筐摆了一溜,装满筐,过台秤,王老呔儿当上了记帐先生,忙得不亦乐乎。看见鲍连长一行十人走了过来,哥俩停住了手,王老呔儿捞把凳子塞在屁股底下,点着了一颗烟。
张财赶紧过来招呼着:“来了,弟兄们屋里坐吧,凤琴哪,给长官们倒点水儿……”
张富:“长官,您今儿个来着了,头喷瓜刚开园,忒好!”又冲瓜窝棚里扔了一句:“长官是来吃瓜的,喝哪路子水呀!”他伸出一只手朝瓜窝棚门口摆了几摆,一边引领着这些当兵的坐到瓜窝棚的西侧凉棚底下。
师爷官同一名勤务兵走近一个梨筐,“悠”地提了过来,几个大兵蜂拥而上,一手抓一个,眼瞅着一梨筐香瓜见了底儿。张富拿一条崭新的洋手巾,托着两个香瓜笑呵呵地看着鲍连长:“刚开园,口头比不上价钱,您先尝两个,不好吃您别给钱!”
鲍庭玺腆腆肚子:“嘛玩艺儿?价好瓜孬!行啊!你小子姓张,对吧?脑瓜子挺活运哪,嘴皮子挺利索呀,你今儿个给我好好瞧瞧,这是个——嘛?说,这是——嘛?”鲍连长伸出右手,在众人面前晃了晃,然后猛的一下松开,一块儿刺眼地炮弹弹片儿呈现在众人面前。张富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长官,这是块铁片儿?”
鲍连长右手托着这块弹片,左手食指点击着:“嘛玩艺儿?这是块炮弹皮子!在你家瓜园地头那棵榆树上扎着,新鲜的,一点锈——还没来得及长呢,你怎么说呀!说你嘛也没看见,嘛也没听着?!”
张富一脸茫然的样子:“长官,就像你说的,我们真是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着,听长官的意思,我们瓜地里落了炮弹了?哎呦呦,什么人要对我们下毒手啊!”
鲍连长奸笑两声:“哼—哼—哈哈——!……真没听见?一丁点动静也没发觉?比打雷的声音还脆生,你们就是他妈的没听见!得得得,本连长今儿个也不是上旨下派调查这个事儿来了,你们不害怕我就更用不着瞎操心了!称两筐瓜带着。”又指了指师爷官:“什么价,问了吗?跟我出差,白吃白拿不行。”
张财挑了一颗周周庄庄的香瓜走过来:“鲍连长,你可真是爱民如子啊!您尝尝这个瓜,口头好啊——芝麻拌蜂蜜,要不怎么叫‘芝麻罐儿’呢!来来接着,用这把刀打了皮更好吃……长官,您手下的弟兄刚才吃的那一花筐香瓜还没有来得及过秤,大概有四十斤吧!您看……”
鲍庭玺:“嘛玩意儿?到了瓜地哪有不吃瓜的?青瓜裂枣谁见谁咬,过什么秤?看什么看?我问你,这两天国境线上消停不消停?两边儿都没出什么事儿吧?你说我当个连长管这么二百来号人,说是巡边守界,好吗!防区的国境线好几百里呀,别说是守啊我巡也巡不过来呀,咳!跟你们说这个干嘛!”
鲍庭玺连长三口两口吃完了香瓜,告诉弟兄们算了两筐的帐,扔了一句:“下个月开响还你们瓜钱”说完抹嘴走人,一行人马撤了。
张财一脸懊丧,愤愤地说:“说得好听,‘不行白吃白拿’!妈拉个巴子,可惜了那三筐香喷喷的开园瓜啦,白白喂了这群灰狗子!”
张富无可奈何地一笑;“他妈的,忒好,这是逼着我去军营做客去,到时候我就给他闹腾闹腾,看看谁丢人!”
王老呔儿目送着鲍连长一行离开了瓜地,心情开始顺畅起来。张富走了过去,眼睛“咔吧咔吧”地问:“老叔,这狗日的连长眼睛挺尖呐,也不知道他能猜中点儿啥,这老小子没往下问,你分析分析他这是什么意思?”
王老呔儿说:“三侄子,不是吹牛皮呀,那个老小子的花花肠子我一清二楚!跟你说,边界上的事儿有些个你不知道,有些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那个老小子保准儿知道,为什么?上边儿告诉他呀,底下有眼线哪,那二百来个兵也不白吃干饭呐!所以说呢,南地头的那摊子事儿瞒不了他!扎在榆树上的一块弹片他都能抠出来,现场磨乎的那么蝎虎他能看不出来?这老小子奸着呢:事多不如事少,事大不如事小,事小不如事了……他是装糊涂呢!”
东升贸小伙计长贵提着两瓶子酒朝瓜窝棚走来。
小伙计长贵招呼张富:“接着!”
张富紧走两步迎了上去,接过酒来,笑眯眯地看着长贵,问到:“是老掌柜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我猜,你是奔我来的!有什么心事跟爷们儿我讲讲。”
“我舅派我来的,想看看你也是真的。”
“怎么样?出来转转心情老好了吧?来,跟爷们唠一唠!”
长贵心情确实不错,在整个金花高丽皮货口集镇子他就跟张老三——张富对撇子,听说老张家瓜地今天开园,特意给拎两瓶好酒来,这两个人有三个共同之处:一、个头般配,体形容貌都差不多。二、都是脑袋好使、嘴皮子会说那伙的,俩人一到一起那话题儿就像大泡子的浪花一样,滔滔不绝。三、长贵吹口好笛子,张富拉一手好胡琴儿,俩人在那块“丝竹一配”常常惹来半条街的人听曲儿。
长贵说道:“我说哥子,你就别装大辈啦,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弟,咳,你不想我我还想你呢,辛苦一春带八夏啦,恁们好不容易把瓜伺候大了,老掌柜特批‘溜上七十度高粱烧’两瓶,怎么样?够高看的了吧!”俩人嘻嘻哈哈地跑到瓜窝棚西凉棚里坐了下来。
张富问:“咱们多长时间没在一起练了!这家伙忙的,打开春我就没闲着过,他妈的,还是这几天晚上看瓜地的时候有工夫拿出来拽吧两下;你呢,你晚上还练笛子吗?”长贵顺裤腰里拽出那根短笛,凑到嘴上试了两个音,撺掇张富:“哥俩整一个曲子,就算是给老瓜王礼祭了。”俩人珠联璧合地奏了一曲河北民歌《小放牛》。
张富收起胡琴,乐滋滋地看着长贵说:“晌午饭搁这儿吃!不行咱俩也整两盅!”
长贵:“不行不行!酒一点也不敢沾!在外面吃饭就更不行了!说说话我就走。”
二十七
张家大院里,老太太在倒乍内精心精意的伺候着两名俄罗斯女人,洗脸、洗手、洗脚,三个媳妇的几件贴身内衣也摆在了那里。
老太太自言自语地说道:“哎嘿!这可挺好!这时晚的精气神可是强多了!不大离儿!哎嗨!——好了吧!快点好了吧!”确实,玛丽亚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脸上能看到几丝红晕,眼神也从忧郁变得刚毅了。费琳娜已经能够用左手抚摩玛丽亚的额头了。能看得出来三个人都很高兴和平静,似乎都有话要说,又终于没有说。
在张家瓜地,几名苏联边防军人越过边界,踏上了南官道一直朝瓜窝棚走来,张富数了数,戴大沿帽的有两名,其余三人戴着船形帽。
张财赶紧走过去对正要放桌子、置凳子的妯娌俩示意停止,小声说道:“别整了,赶快收拾回去,你俩也躲一躲!”向坐在房檐后纳阴乘凉的王老呔儿通报消息:“不好,又来了一帮毛子兵!”
“不要慌,我估计不会有什么事,你先支应着,我听听他们说什么。”王老呔儿依旧坐在后墙阴凉处,他要听一听这些苏联士兵讲些什么。
张富站在明处眼睛瞪得老大盯着几位苏联军人,他别楞着脑袋问王老呔儿:“老叔你说,这南国界赶上什么啦?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什么时候,说进来就进来,说出去就出去,这不是‘秃尾巴卖栏——没裆了’吗!”
王老呔儿把双肩一端,摊出一只手,把眼睛往上一挑:“三侄子,这事情可就不归咱爷们管了……听说,这条国界……中苏两方的官家都不主张扎死;我还听说,从前清时候起,两国就有协定,双方各留二里地做自由贸易区,允许两国老百姓在国界上自由来往做买卖,还不用交税;你就说咱金花高丽这块地方吧,,不让进了;,过了火车站再想往里进就得另外交税了;嗨,一句话,都是为了做买卖!人家得买,咱们得卖!嗨,寻思这些个事情干什么!只要两国边界上太太平平的,就是你们的福!赶紧答对洋客儿去吧。”
张财嘱咐两位女眷躲进瓜窝棚里,自己搬过一条凳子坐在门口,掏出小烟袋儿吸烟,张富、长贵爱瞧新鲜、好热闹,俩人迎上去,长贵用简单的俄语打招呼:“达瓦利息,得拉斯维基!……”
为首的苏联说了一串儿俄语,又拽把凳子坐下来,其余四名苏联军人也找凳子坐了下来,长贵说:“这个官……话说的太快,不好懂,他们肯定是要吃瓜,唉!老王老舅呢?”
张富:“先别露他。”又朝张财说道:“二哥,你把抬秤拿来,泡一筐瓜, 叫他们先吃了,给不给钱就看他们的了。”
长贵说:“三哥,,不过你糊弄他不行!他们认死理儿。”
五名苏联士兵有滋有味儿的嚼着香瓜,不时地说几句满意、赞美的话,当然没有几个人能听懂。
苏军士兵大都来自于工人农民,是苏联人民中的普通平民,善良、诚实、直率是他们的典型性格。当然,某些时代的影响、某些历史的传承、某些民族的隔阂、某些个体人因为完美性格尚未臻成——因为理想道德操守的缺失而产生的狭隘、偏激和贪婪意识,常常会强烈地影响和左右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因而,有些人常常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沙皇式拓张情绪和大苏联情结也就不奇怪了。
一名年轻的士兵向他的同伴开玩笑:“(俄语)战事平息了,伟大的苏联迎来了彻底的和平,我就到这里来种瓜,娶个女人,当然是娶一个中国女人,不,娶两个,娶三个,我听说中国的有钱人可以娶九个老婆。”
另一位同伴儿讥笑他:说他太没有苏联男人的气魄,他要是到这里来,就办一个大农庄,生产好多好多面包、香肠、牛奶、黄油。
一位长着凹斗脸的不屑的看着他的士兵,用很轻松的口吻、很坚决的语气教训他们说:“(俄语)都可以做,不过都不会有大出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把铁丝网挪一挪,你的面包、黄油、你的那个好吃的甜瓜还有女人,当然就永远是你的了,伟大地俄罗斯军人胸怀要更宽阔一些,眼光要更加远大一些。”
另一名四方脸梳着小胡子的眼光深邃的望着他,一脸的鄙视,像政治家一样解剖他的话:“(俄语)你是说,要我们,那些苏联军人去为你们这些贵族老爷开疆扩土!一个混蛋的混蛋逻辑!该死的沙皇侵略扩张得还不够吗?!让你的贵族老爷的胸怀和眼光见鬼去吧,别忘了现在已经不是沙皇俄国时代啦。这个世界也不是过去的世界了!”这位年轻的苏联激动得满面通红,他抬起头来鄙夷地盯了对方一眼,大口大口地咬了几口瓜,把瓜屁股狠很地摔到了地上。
张富走过来小声地告诉张财:,就是那天晚上到咱们瓜窝棚搜查的那个人,也不知道他急头掰脸的说些什么?”
几名苏联军人很快就吃光了一筐香瓜,看得出来他们吃得很高兴,谈得也很高兴,海阔天空口无遮拦,有很多是玩笑话,是当不得真的。
王老呔儿自始至终地听完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内容,他了解苏联人的性格,幽默、欢快、放浪、无羁:“不过,那个凹斗脸的混蛋说的‘铁丝网’的话有点出格,有点令人不安;这个兔崽子忒不是东西,他的话只能代表他自己,像这种狗日的苏联人越少越好,妈了个比的,‘铁丝网’是随便挪的!”
王老呔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象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张富说话,听得张富一头雾水。然后又掏出香烟来吸着,心中若有所思。
等到几名苏联军人离开以后他从墙后闪了出来,问到:“给的什么钱?”
张富凑过来说:“两块银元,老叔你给看看,这东西管用不管用,我二哥直捅咕我,可你不收这个东西收啥呢,你总不能跟他要哈大洋吧。”
长贵也凑过来说:“我见过这种银元,,我没说错吧老舅?”
王老呔儿接过一枚银元,仔细地看了看,敲了敲,听了听,说到:“不错,不错,忒合适了,按理说一筐瓜怎么卖也卖不上这个价。”
接着他把五名苏联军人的几句关键性对话告诉了他们,他们先是楞了楞神儿,然后便相互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表达的意思十分清楚:吹牛‘逼’,说大话,你挪一个试试,来吧,狗娘养的,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们。
二十八
张财把马车赶进了张家大院,车上坐着他的媳妇凤琴,凤琴冲东屋喊了一声:“妈!叫接你上瓜地去吃饭呢。”
俩人直奔东屋,见屋内没人,张财说:“去倒扎看看。”
凤琴朝里探了探头,费琳娜作了个要喝水的手势,却不见婆婆在里面,她一边去舀水一边告诉张财:“咱妈没在里边,你到后院找找。”
老太太正在后院忙着一捆一捆地抱秫秸,一身的灰尘,一脸的汗水,张财一看,诺大的秫秸垛已经被拆开了一小半儿,一捆一捆地秫秸被立在了通往茅楼的杖子上:“妈,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活让我们干哪,大热天的累坏了怎么办。”
老太太笑摸滋的说:“你们不是忙吗,我寻思啊,那两个人今后免不了出外头解手撒尿什么的,杖子又不严实,来来回回的让外人看见不好,咱家柴火多,蒿子杆儿、高粱挠子、豆秸好几垛呢,我寻思用这些高粱秸把杖子加高加密,咱们后院子里的人和事儿可就走漏不了风声了。”
张财心里惦记着瓜地,说:“妈,叫凤琴看家,捎带伺候那两个人,您跟我坐车上瓜地,我老王老叔八成也在那呢,你不去不好,我到前院子等你,你洗把脸,咱们就走。”
晌午,张家瓜地瓜窝棚前面,人们把两张饭桌拼了起来,烧酒、鱼肉、菜蔬摆了一大桌子。
王老呔儿把一个油光铮亮的双层食盒交给了老三女人,牛皮轰轰的坐了下来。
秀芹、玉珍把饭菜答对齐整了,领着三个孩子进了瓜窝棚里胡乱地吃吧了一口——老张家规矩大,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女人和孩子是不能上桌陪客的。
老太太心情不错,喝干了一小碗儿烧酒,老三张富不喝酒,所以话也少,闷着头吃了两大张葱花油饼。
王老呔儿心情好极了:“我说——侄媳妇!把‘字’个滑溜里脊、拆骨肉给孩子端过去,好东西不能光可大人造……”
他酒量好,又特别喜欢这种家庭式的饭桌气氛,话也就说的多了些,他特别喜欢大泡子里的“罗锅白”:“老嫂子,也不知道咋儿回事,我忒爱吃这种‘大白鱼’,你们叫噘嘴骡子,在我们老家,就叫捣子,个头小多了,味道也差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这块儿的人把这好东西糟贱了,都嫌呼这种鱼刺儿多,油少,不少人家把这种好鱼都扔猪圈去了,其实要我说呢,满湖的鱼,就属这种鱼名贵,肉又白,口味儿又鲜,吃起来肉是脆的……!要那么香干什么,图意香,吃肥猪肉啊。”
张富见母亲也吃完了饭,便打个招呼跟母亲下了桌,对老太太说:“妈,忘了个事儿,忘了给我爹和大哥上坟了,怎么办?”
张财“哎呀”了一声,说:“妈,我现在就套车上坟茔地。”
张富:“二哥,你不是没喝完呢吗?你陪着老叔喝酒,我跟妈去就行了。”他拎过一瓶烧酒,跟老太太一前一后的朝马车走去。
王老呔儿手里端着酒盅朝老太太背影喊到:“老嫂子,喝完这盅酒我就过界了,八月节前也许还能回来一趟,捎啥东西不?”
老太太回过头来应了一句:“啥也不缺,倒是你得多加小心哪,乱马迎花儿的……!”
王长志进屋把几个小孩子扯到桌子旁,把好东西端到他们巴旯。扯着张财,俩人又兴高采烈地喝开了。
王老呔儿喝着喝着忽然情绪低落起来,他看着几个孩子,不无伤感地说道;“嗨!爷爷要走啦!此生注定飘零……下回见……走了!”
未完待续。。。
鸡西新闻传媒集团微信矩阵
【鸡西原创小说连载】金花高丽 ——《大火磨》之风土人情(九)
【鸡西原创小说连载】金花高丽 ——《大火磨》之风土人情(八)
【鸡西原创小说连载】金花高丽 ——《大火磨》之风土人情(七)
点“阅读原文”看更多鸡西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