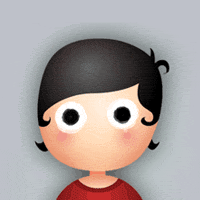我 明 白 你 会 来,所 以 我 等
香飘端午情更浓
作者:鞠勤
○
随着端午节日的临近,端午与人们的感情也越来越近。说端午,道端午,端午趣事,还是童年最为美好。
小时候,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都是要在门前挂上青青的艾叶、柳条避邪祈福。每当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小孩子们最为快乐的时刻,我们成群结队的到田埂上大把大把捋着艾叶,折着艾的枝杆,然后折些柳条将艾草和柳条和柳条绑好,扎成一小捆,扛在肩上,唱着哼着说着心中的小秘密向家中走去,如果碰到了沙枣树,顺便折几枝沙枣花,放在家中,又有了沙枣花那扑鼻的清香。
因为不够高,常常拿个小板凳垫在脚下,把采摘的艾枝、枊条挂在自家的门前,然后再去别人家的门前逛逛。那绿色青翠的艾叶,散发着浓浓的天然香味,好闻极了。
到了晚上,妈妈便要把白天摘来的艾叶、沙枣花和它的叶子、香毛草,还有车前草、蒲公英等泡成水,用来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洗澡,然后在脸上和脚腕、脖子上还要涂抹些用雄黄泡过的酒,那时,可没想到可以驱邪什么的,晚上感觉睡觉香甜了许多。这种传统,到今天,虽然妈妈早已离我们而去,可每逢过节,我们都会像以前那样,到集市上去买些来泡水洗洗身子。只是现在远离了乡土,没有了以前那种采摘的乐趣,童年端午乐事,也唯有在梦里依稀了。
端午节还有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包棕子,那时我们家乡人包的棕子,不像今天那么多种类,那是种纯纯的家乡口味,特别的香。做棕子的时候,先淘洗好米,然后将水沥干,接着在水中将干枣泡软,洗净苇叶,然后,在一个芨芨编制的笊篱中先沿底顺边铺好苇叶,然后一层米一层红枣有序装满笊篱,将苇叶收回把棕子包住,上面压一块洗净的平平的石头,然后将笊篱放入盛水的大锅内,点燃柴火加热,做成的棕子,味道独特,轻咬一口,满齿噙香,透着自然的草木清香,这是家乡的味道,爱极了。如果你偏爱吃甜点,则可在制作棕子时,在其中撒点白沙糖,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平时没有什么好吃的,逢年过节,只要有好吃的,我们就最高兴了。端午吃棕子,还要用从生产队分来的,或家中自产的纯纯的胡麻油炸上油饼,用油饼卷上棕子,用手拿上,吃在口内,香在心中。艾香、棕香、油饼的香味,还有沙枣花的清香,就这么简单,整个端午就浸染在浓浓的香气中,吃着吃着,整个香气却缭绕我们走过了一个童年。
还记得我奶奶,每到端午节前夕,老人就开始找香料,给家里的人缝制香囊、绣做荷包,里面最常装的是香毛草、香豆子等香料。端午节那天,佩带在胸前,香气袭人。那时,我们一家围着奶奶团团坐着,嘴里边吃着香甜美味的家乡棕子,边听奶奶絮叨着家乡的老庄子、大长陵、远坝、灰疙瘩发生的一些轶问趣事。
后来,我们长大了,对端午节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也叫端阳节,端午节吃棕子、赛龙舟,在南方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后来又有了所谓的纪念伍子胥、纪念孝女曹娥等说法。据说,后来又有了悬艾草、插菖蒲、沐兰浴等习俗。北方的端午风俗,似乎更多的是与驱邪避恶、防病减灾有关。关于这一点,随着日月的变迁,我在有关媒体也看到了这方面的知识。似乎这方面的说法大同小异,因为在北方,仲夏五月,毒虫孽长而百病生,正是极易染疾病死亡的时节,人们认为,五月五日是毒月恶日,以至于五月有“不举子”、“不迁官”、“不盖屋”之说。
其实,我对端午的最初认知,完全来自于粽子。以现在的视角,忽然觉得,端午节更象是包裹粽子的苇叶,它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都细细密密地包藏起来,熟透之时,苇叶汲取了糯米的粘质,糯米渗透着苇叶的清香,似端午与屈子之间的浸染,节与人的统一。后来,知道了屈原和楚怀王,知道了《国殇》和汨罗江,每年的这一天,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习俗。
端午节,有着浓浓的历史文化,神州大地上,在端午节前后,便有着浓郁的传统节日风味。人们在欢度端午的时候,更多的是深深的怀念,并伴有一种隐隐而又深深的哀痛,哀痛诗人一生际遇,哀痛人们认为值得的一切哀痛。端午节对于我,也有着别样的情怀。怀念家乡,怀念亲人,似乎总是在特定的节日里更加的浮现在眼前,镶嵌在心里。粽子还是粽子,只是吃在嘴里,心里忆念着故去的亲人,那永留人世的血脉亲情,在这个粽香飘飘的端午节,有着浓浓的思绪飘着,天上人间粽(总)是情。
飘雨的端午,飘香的端午,在今天,又飘来了端午时节的快乐往事,原来美好的事物在我记忆深处从不曾失落,从不曾丢失,就像那串童年时挂在家乡门前的艾草青青,还有那家乡独特的粽子飘香,以及诸多的人情事故,在我的记忆长河里,永远都是鲜活的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作者简介:鞠勤,笔名南山子衿,甘肃张掖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张掖市第四中学。2009年开始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出版有散文集《岁月的声音》以及儿童经典悦读系列读物《幽默笑话》卷。甘肃省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近年来,发表作品200余篇,作品多以散文为主,散见于《甘肃日报》《北方作家》《中国教师报》《未来导报》《张掖日报》等报刊杂志。喜好书法,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张掖市书法协会会员。在全国硬笔书法等比赛中多次获奖。
彩蛋分割线
近本公众号赞赏功能开通,致力于原创
其实就是发声者原创的一篇文章
感谢关注者厚爱,最请多指教
风从故乡来
小三子,破伤风了。
尽胡思乱想,嘴里的大豌豆已经半天了,还是整个儿的;
全身疼,不敢下炕,怕风。
四躺八仰,迷迷瞪瞪······
朔风温柔下来,河面的冰乘小三子不在,偷偷开裂、消融,咔嚓——春雷一声天下惊。
春天的风是从那场春雨之后开始的。万物复苏,老鼠和蛇,从蛰伏中醒来。
大约是谷雨,小三子的姥爷,会扛一把䦆头,到湿润的地里,开垦土地,倔老头的汗珠子,风一吹在地上没有摔八瓣,反而融进去了,不声不响地,和人一样。
天黑黑,翻下炕就是走,吆起站着睡觉的毛驴儿,带上犁铧、干粮,都睁着大眼睛,顾不得揩眼角的屎蛋蛋,凭着记忆,摸索着走,渐渐可以看见黑黢黢的山、灰白的路。总有人已经在远处扬鞭,吆喝声、鞭声回荡山谷,但那鞭从来没落在牲口身上,不然不会那么响。
河谷里吹来的夏天的风,常常会有暴雨,风是雨的头,长辈们都叫他“白雨(暴雨)”。可能是这些雨下到地上有很多的水泡泡,就像来自外星的航船一样在雨的流水中漂泊出水渠。记得有一回,白雨中小三子的姥爷穿着一身旧式的中山装,小三子在偏房看着那身中山装格外的崭新,那是因为姥爷在雨中没有奔跑,一路从暴风雨中走回了家。
雨后,小河里头,河水丰盈,地皮的光晃得眼晕,冒着蒸汽,猪儿和蛇都懒懒的不动。整个河谷都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空洞的山窟、老树喃喃着摇篮曲。小三子和小伙伴们,会脱的光溜溜,扎进水里。河水旁的洞洞边,有只和小三子脑袋一样大的蟾蜍安详地看着一群后生。每每回家后,家长都会查看有没有调皮去“打搅洗”。家长眼里,小河经常发洪水,郑重其事的检查小三子和他们小伙伴儿的耳朵背后看有没有淤泥,其实家长小时候没少在河里洗澡澡。后来,小伙伴们都知道了这一招。每回在河里游玩之后,一定着重的把耳朵背后洗得干干净净。
秋天的风里头,掺杂着麦香。人们在忙着收麦子。从高高的山上。用肩膀扛下来、用独轮车推下来、用架子车面套着驴把他们送下来,然后摞成佛台一样的麦垛。
农村里,一年当中有两件大事不得不提。一是打场。
这也是最需要防止“白雨”的时候。有暴雨一定得及时收场,不然,雨水会帮农人们将已经长了一年的小麦全部混杂在雨水里头,变成那种发芽的麦子,现在很多人喜欢吃芽面的面包,可能就是雨水的恩惠。
一户人家往往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麦子全部变成麦粒儿,需要好几户人家在一块儿去做这件事情,那一段时间,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石碾子碾过那些麦秆之后,麦秆儿变得松软温柔。孩子们便可以尽情的在其中撒欢儿打闹翻跟头。并且在这一段时间里,各家各户都把自己家里拿手的凉菜、饮料以及水果一股脑儿带到麦场里。
小孩和大人一起在背阴的麦垛后吃着午饭,甚至可以偷偷跟着那些老烟枪感受一下“老汉烟”“炮筒”烟草的味道,往往被呛得流出眼泪,但这或许也为他们未来喜欢上这个味道,埋下了种子。
秋天的风里头还有甜蜜的气息,小三子爬在树上乘凉,像只抱紧树枝的猴子,净想着姥爷给他准备的好牙祭。果园里的桃子,个个好像是潘桃园里出来的,还有家门口的那棵大娇杏树,在马路边格外的鲜艳惹人。其他的小伙伴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小三子特别幸福,他能够独享这些美妙。秋天的果园里,长满一树一树的诱惑。摘果子也是有技巧的,轻轻往上一掀,果子的把儿就和母枝分离了。有些果子成熟之后,风轻轻一吹,它就会坠落到地上,姥爷告诉小三子,这些果子味道最香甜,浸透着一整年的阳光味道,是糖心儿。
很多年里头,秋天都是丰收的季节。但有些东西慢慢的凋零不易察觉。就是在一个秋天里头,小三子的姥爷跟阎王爷犟了三个月,直到庆贺丰收的时候,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天晚上,天空中下起了暴雨。
中间还有一些冰雹。记得那一天,小姨在雨水里头跪着,一直哭着,雨水悄悄地把泪水里的碱冲淡了。
秋天的风吹拂了事,接下来是越来越冷的天儿,农人们要为过完整个寒冷的天做准备。果树的枝条晒干码好,好作为一整个冬天里头烧炕烧炉子的用量。
冬天的时候,火炕、炉子、灶台都是红旺旺的火,在这里头煮着春节。
过年、除夕、压岁钱、放鞭炮、烧头香、吃肉、包饺子,那些风,虽然刮得紧,但屋子外银装的景象也觉得暖意融融。
小三子最喜欢的,是春节之前。在火炕里头,红红的柴草堆上烧着一只田鼠,撒一点盐就是人间绝美的味道。在炉子底下的炉灰里头,煨一颗土豆,外层有些焦,里面散发着热气,熟稔焦黄,粘口美味。
更不必说在春节的时候,天气寒冷,天空中的烟花,还有烧头香时候的人头攒动。
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信仰,那就是来年会更好。风会吹拂着那些香头,显得那么的香火旺盛。但在这个节气里头还有一样东西一直流传着可能很长时间了。就是在村子里头有哪一家有人过世了,初一初二初三大年的头三天里头,村子里头的年轻力壮的人都会结伴到这些家里头给故去的人去烧香磕头拜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三子跪在炕上,脖颈强直,脑袋埋在腿间,满嘴角“苦笑”·······
作者简介
牛健刚,甘州区广播电视台播音员。生于通渭,长于天水,学于河西。读书期间偶有作品发表于校报、《通渭文化》,大学期间致力于播音主持及全民阅读。今拾笔墨重笔耕,不惧见笑于大方之家。
图文原创,转载请联系1556980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