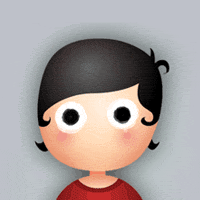快起来,跟我去拔草。不洗头吗?洗的头发黑黝黝的,辫上辫子多好看。
姥姥在炕头上念经一般,让我没法再装睡,只有醒来。即使醒了,也不立即下炕,而是在炕上磨蹭上半天,隔着玻璃看看窗外的天气,然后嘟囔说天要下雨,草拔不成,还是算了,就不洗头了。说完又会倒在枕头上。
姥姥见我动弹后又倒头,说话语气加重,咔(迅速的意思)地起来。我一听,像上了发条一样,从炕上弹起来,三两下叠了被子靠墙放齐整,又铺开小被子,跳下炕,那麻利劲,惹笑了姥姥。
瓜丫头,你被电打了吗?姥姥笑得像花盆里的长寿菊。
我不理会姥姥,快速抹了一把脸,没有刷牙,农村人谁刷牙啊?不刷牙的,要是去亲戚家吃酒席或是进城,至多用盐水涮涮。我在10岁之前是没有刷过牙的,看到父母刷牙,白色泡沫挂在嘴角后又擦掉,觉得有些做作。心里嘀咕,姥姥一辈子没有刷过牙,也没有见过牙不好。我以后也不刷牙,进城拿盐水涮涮。
我的洗脸水大概能掬起只有两捧,我噗噗地在脸上抹搓两下,水就所剩无几。脸盆里脏兮兮的一点,潲在堂屋地里,潲成几朵花花。然后用毛巾揩一下脸了事,也不抹油。其实没有油,没有宝宝霜或是郁美净,只有棒棒油。我不抹棒棒油,一来不喜欢那味道,二来抹了脸上油光发亮的。乡下到处都是土,棒棒油遇到土,一搓一层垢甲,更脏了。 洗把脸也浮皮潦草,一点也不认真,像猫洗脸。姥姥嗔怪我。
猫洗脸只用唾沫,我用的是水。我反驳姥姥。然后拿过木梳,不解头绳,站在炕洞前,在头顶上胡乱刮一下,想着反正要洗头,刮一下省事。
姥姥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看着我,也没吭声,但是我要放木梳时,一把扯住拉过,我斜着身子挣脱也没有成功,最后服帖地蹲在那里,被她用双腿夹住,给我梳辫子。
姥姥拿起梳子一手捏着头发,一手举着梳子,一下是一下,头发服帖地在姥姥指端飞速成小辫子。
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跳到草房,拿了铲子,提了栲栳,跟着姥姥走向村外的田野,去拔草。
端午节的清晨,就这样在姥姥要拔草而上演的故事中推开了。
姥姥属于身材高挑的人,即使下地干活,她的背也不像村里的那些阿奶和大婶们那样驼,总是直直的。我有时会跟在她的身后,故意翘着脚尖,脚后跟着地,一颠一颠地迈着碎步走。每次,姥姥发觉时已走了十几米了。
姥姥会斜着身子抓我,每次,我会大呼小叫,喊着边上的草能洗头吗就跑开了。
我还问过姥姥,把步子迈大一点,少走几步,干嘛走碎步。姥姥也不作答,眼睛盯着路旁的草丛。
其实,拔的草很普通,叫白蒿,有股淡淡的味道,白蒿边总是有荨麻挨着,怕丢了似的,白蒿在哪里荨麻就紧紧跟到哪里。都说一物降一物,荨麻是冷血又挑衅的植物,喜欢扎人喜欢进攻。一不小心被扎,奇痒难耐,唯有揪了白蒿,揉蔫了擦擦就好了。
姥姥拔了一些白蒿扔进了栲栳,我也扽了几根冰草,问姥姥拔不拔荨麻?
姥姥没有理睬我,继续在地脚边拔驴耳朵,我也不再故意问了,见了白蒿打尖。驴耳朵贴地而长,不好拔,姥姥拔的也少。
田野田野,除了麦田,除了庄稼,就是野草。那么多的杂草,能拔煮水洗头的不多,但很快栲栳就满了。姥姥让我先提回家让烧大锅先煮,她一路走走看看溜达着回家。
我到家时的早饭已经熟了,所以草还没煮,姥姥也到了。提着几根柳枝,让表哥在大门上,说是五月端午的习俗。
因为过端午节,要吃好一些。早饭是炸油饼,炒的洋芋菜,还做了凉粉,早饭后还要做酿皮。凉粉和酿皮是晌午饭,油饼和洋芋菜算是早饭。
等我端着油饼到堂屋时,姥姥从她的箱子里拿出了她的存货——一本夹着多彩丝线的旧书。吃饭前要戴花线,姥姥在用她的丝线拼色,大红、明黄、浅绿、海蓝、黑紫、粉白、玫瑰红等颜色的丝线,姥姥一根一根拼到一起,与搓了,先给表哥戴在手腕上。由于细线较短,只能拼一次戴一下再拼。
每次都是表哥的左手腕上绑了,右脚腕上也绑之后,才给我戴,两个手腕,左脚腕,空着右脚腕,我要戴,姥姥说绑死了就长不大了,戴花线是为了不让蚊虫和毒蛇叮咬。为了快快长大,为了不让姥姥再以唾沫做水给我梳头,为了不让蚊虫叮咬,我顺从了。
然后是戴,姥姥最后才戴,她只戴一只手腕,然后把剩下的线头绑在中指上,说是戒指。
最后,姥姥才拿出一个桃红色的荷包,香喷喷的。给我绑在第二颗纽扣眼上,我拿着,一闻再闻,特别喜欢。姥姥说是松香,蚊子们不喜欢松香味,见到我会躲开。荷包与花园里开的荷包牡丹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两绺绿莹莹的穗子。我高兴得头发都渗着笑,早上被姥姥口水捋顺的头发也不再臭烘烘的了。
俊啊,荷包跟姥姥一样俊。我夸着看着荷包,想象着戴上荷包丝线,走在山路上,蜘蛛、蛇、蚊子等统统躲到一边,别提多美了。
草草吃了早饭,太阳也一竿子高了,煮好草水时,太阳已经照在檐下,于是姥姥给我洗头。草水兑了冰水,黄绿黄绿的,把头发浸湿了,碱面一样要抹,揉搓也难免。好几天才洗一次头,水黑乎乎的。姥姥的手劲大,搓得我头皮疼,洗两次后,才用清水冲。冲时还是加点草水。我觉得没有洗干净,反而脏兮兮的。嘟囔时姥姥会在后脑勺拍一下,说端午的草水洗头,头发黑亮黑亮的,不生虱子,再擦擦身子,土虼蚤不叮。
我答应着,揣摩着洗了头出去显摆荷包,所以不多言。
头发还没干,我溜出家门,快速走到大核桃树下,见只有两个年轻媳妇在那里拉话,就一手托着荷包,一边做着闻的样子走过去。她们看到了,眼睛发亮,我立即掖进衣服里,故意走开。然后又在论事台前取出来,用手挑着,走一圈,最后对着隔壁的大妈站在那里。
大妈一看我的荷包,再看到我的花线,立即拽我过去,提着荷包端详了一下,再扯着花线,用拇指搓搓,说你丫头命大,这荷包做得这么好,花线这么俊。我一听,要过我的荷包,说一家人都戴这样的花线,然后跳几步,离开论事台,跑回家。
村子里姥姥拼的花线最俊最好看,丝线也是最好的。村里的大嫂阿姐们很是羡慕,我很得意,跑回家告诉姥姥。姥姥并不高兴,说那么好的银线,戴在腿上有些糟蹋,那可是你太太给的陪嫁,从外地带来的。
……
每年的端午节,姥姥要拔些草,煮些草水,要我们洗头发,她自己也洗头洗脚,雷打不动。她这点被母亲记住,这么多年来,除非下雨,否则,她还是会走一些路,拔些嫩草回家,也是煮了,让我们洗头发。起初是我们洗,后来就是侄女洗。
洗了很多年,也没见头发黑黝黝的,相反,偶尔一冲动,染色继而烫一下,头发像荒草,散乱,即使新长出的那一截尽管是黑发,却无光泽,别说黑黝黝的,倒是白发首当其冲,又硬又粗,义无反顾地簌簌生长。
今年的端午,母亲会走好远的路去郊外,拔草煮草水让我再洗一次头发吗? 我思忖着,数着端午节的日子,我有些惆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