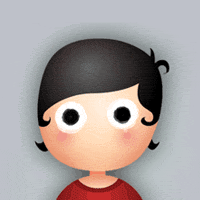点上方蓝色字
一进入六月,不知有多少家长的心,又要马上提到嗓子眼上,一年一度的高考快要开始了。
其实这个时候,还不是最热的时候,从温度上说,心情可能还稍微稳定一点,但那些年的高考时间很奇怪,是七月的七、八、九号三天,是天气最热的时候,热得人心烦意乱,决定了好多人命运的高考就在那几天进行!
一中,通渭的最高学府,大名鼎鼎,班多人多,高三年级尤其多,一般有十七八班之多,每班均为近八十人的超大班级,座位满满当当,足插不进,水泼不进,如果不是那些学美术、考体育的经常在店家睡大觉,估计教室都难容其足,清楚地记得整个学期,大概只彻底扫过一两次教室,平素只有感觉太脏的热心同学,拎几桶水从前往后一泼,算是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当年的一中新教学楼)
其他年级的学生都在敞亮的新教学楼里上课,而高三年级所有的教室,都是平房,且年久失修,地坑深陷,自北向南,集中在操场南端,这让高三愈发有些头悬梁、锥刺骨的感觉。每到课间休息,大家只有感觉上厕所极为方便,男同学在东侧延墙根绵延数十米,就地解决,全没有了文人的雅致,女同学低头侧目,匆匆而去,匆匆而回。偌大的操场,几乎成了高三学生的专场,除了早上跑操时能见到其他年级的小孩之外,其余时间他们像小鸟一样,不敢越操场半步,此处全是高三“老大“的天下。
一中的老师们非常有特色,朴实认真,不苟言笑,大多写得一手好字,上课时认真讲课,下午放学后急忙挑水,一手课本,一手扁担,角色转换非常自然,全不会有为难之态。上课时要么本地土语,要么全是英语,很少讲普通话,每节课乡音绕梁,不绝于耳,眯眼倾听,也算是一种享受。
语文老师快要退休,头顶软塌塌的蓝帽,身着干净的蓝色中山装,喜欢走下讲台,边走边用高分贝的乡音尖尖地读古文,读到高音处便没了动静,眼珠也稍变得白一些,这时身边的同桌便会无可奈何地低声说一句:“唉!像老哇(乌鸦)!”
数学老师胖胖的身子,登上教室台阶时像胖娃娃一样,得扭一下屁股,每次走进教室,未及开言,就已经咧着大嘴,似小孩一般口水湿着嘴唇,笑容满面。讲题的时候逻辑极为清晰,胸有成竹,左比右划,兴致勃勃,唾沫星四溅,讲着讲着就讲到自己的老婆烙的油饼子上去了。那时工资常不及时兑现,老师们周末便到乡下去拿干粮补贴一下,真是可怜!
上历史课之前,同学大眼瞪着小眼,努力压制自己不能笑出声来。温老师推门而入,只携一本课本,最多两支粉笔,径直拾足而上讲台,写几个字之后便转身直视后墙,呈立正姿势,目不斜视,开讲:
“嗦,大概呢!八国联军呢,闯进北京呢,园明圆呢,遭殃呢,盆盆罐罐呢,全打碎呢!”然后深吸一口气,盯着后面的房顶,继续说:“嗦,大概呢,慈禧老佛爷呢,麻烦呢,跑呢,一跑呢,跑远呢,跑到西安呢……”
整整四十五分钟,纹丝不动,书也未曾打开,黑板上也不再多写一字,内容全部讲到,铃声一响,拾步下阶,推门而出,身后是目瞪口呆的一室乡下娃娃。
胖胖的年青英语老师,长满了络腮胡子,同学们戏之为“马克思”。 据说在校园、在课堂上他都是一口英语,很少听到他的“本语”,甚至有同学在厕所偶遇,也会手足无措地试着用英语和他打招呼,且不论他英语水平如何,单是那酷似马克思的形象,亦足以说明一中大师云集,可惜没听过他的课,据说是一种享受。
有一位婀娜多姿的女教师来自天水,肤色白晳,常说普通话,与丈夫同在一中教学,听说当年在谈恋爱时,男方大吹特吹老家的一中门前,有块波光粼粼、柔柳拂面的“西湖”,让这位女同学浮想联翩。后来俩人成了,亲自来此一看,其实是个垃圾环绕的涝坝,就连块池塘都算不上,一泓清水更是影都没有。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校园里的她时常一袭裙装,成为整个学校为数不多的装扮,每当走过操场时,便有许多在屋檐下纳凉的男同学齐声开喊:“一二一,一二一………”这位年龄不大的老师便停步瞪眼,喊声顿息;碎步而起,喊声再起,如此二三,身后笑声一片,她也宛然一笑,粉面而去。
物理权威是大名鼎鼎的牛老师,讲着讲着便在黑板上随手几笔,画一幅山水画出来,画风大气磅礴,结构精巧,气势不凡,班上的同学便自豪地说“不会画画的老师,不是物理好老师!”
(奋笔疾书的田应龙校长)
田校长身后从来不缺追随者,他出现时经常抱着一卷刚买来的宣纸,边推小会议室门,边随和地说:“我给咱写!我给咱写!就是写得不好么!”随后便叨着一支香烟,眼睛微眯,展纸泼墨,大笔一挥,每写完一张,拎起来,眯着眼瞅几下,然后顺手给旁边围观的学生、老师,说道,“暂给你拿着糊墙去!”
有位同学在紧张的高考备战前夕,还醉心于自己的地震波研究,每天偷偷潜入一口废弃的水井中做实验,时间不久,外国的一家什么机构竟然寄来了证书,吓了老师、同学们一大跳,红纸喜报贴在门卫室的墙上,一时睹者如云,赞不绝口。
同学们除了课堂努力之外,也时不时地找几名家在县城的同学,挤在黑白电视前,收看北山转播站专门为高中生播放的名师课堂,一个个目不转晴,时而托腮沉思,时而奋笔疾书。那么认真,渴求知识,真是让人永志难忘。
那时一中的校内没有住宿条件,来自全县各个乡镇的同学,便零散地租住在不大的县城,东起陇阳路口的东川,西至二中附近,南至南桥头,或三两人或四五人,一个土炕,些许行李,除此之外便只是几本书而已。
同学们的标准配置是一个煤油炉,一口小铝锅,几根长短不一的筷子,一块或是三合板或是硬纸壳做的菜板,擀面杖可能就是一个啤酒瓶,有些同学碗都没有,经常锅就是碗,碗就是锅,合二为一,既快捷又少了洗碗的环节。
口粮一般是从家里捎来的土豆和白面,没有任何其他的蔬菜,通常的做法就是土豆炒洋芋,面条加面片。做饭的流程非常标准、快捷,先在小铝锅滴入清油三两滴,稍热锅,从水中捞出不管洗净是否的洋芋,放入热锅中,只听“扑哧”一声,筷子两搅,再倒入凉水,边烧水边和面,然后用绿色啤酒瓶稍擀,水开以后揪入,煮沸,搁盐,灭火,然后端起锅放在一块纸壳上,开吃,几分钟之后一扫而光,马上背起书包上学校,行云流水,不落他途。
通渭县城缺水,而且一分为二,城南城北有苦水甜水之分,如果所租的房子正好处于苦水区,那就得忍受常年拉肚子的难言之苦了。如果偶然有甜水做饭,就好似世道换了人间,所能改善的,就是找房东要点浆水,做一顿浆水面吃,也算是能改善一下伙食。
吃是如此,住也好不到那儿去。夏天时老天照顾,没有个电扇空调什么的,反正也热不死,冬天可就不好过了。
许多同学租住的都是土坑,一到冬天,寒风凛冽,北风怒吼,冰冷的土炕尤为透心凉。但烧炕却没有柴禾,城里人本来就种地很少,房东也无能为力,同学们便想了好多办法,比如与房东商量,问是否能用电褥子,如允便上市场买来电热丝,左右比划,自个缝制。如果费用高或别的原因不让用,那就再想想办法。更有甚者讲,可以用铁钉制成土暖气,从灯泡上接电线拉到盛水的脸盆里,烧些热水,不知那是在困顿中冒多大的风险而出的智慧。
一般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同学们就已经到校开始自习。教室很大,电灯很暗,由窗外看时,好多同学的桌上放上了一盏煤油灯,星星点点,蔚为大观。天刚麻麻亮,早读的同学便开始在晨曦中朗读,全然不顾身边的他人,不小心踩个脚或碰个头也在所不惜,整个操场弥漫在朗朗读书声中,如同辛勤的蜜蜂发出的振奋之声,用通渭人的话讲就是“狗头蜂钻到瓦罐了”。
到晚上晚间自习之时,也如此一般,照样地灯火辉煌阑珊一片。夜静更深,门卫师傅都困了,晚间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就断了教室的电也关了校门,这时候大家又一个个小心地从书桌里拿出煤油灯,小小的油灯愈发可爱,在漆黑的教室中闪烁着一点点红光,照耀在苦读的脸庞之上,那样的静谧、温暖。到午夜时分,困倦难耐时,同学们便开始三三两两地翻校门而出,衣兜中的煤油灯也免不了上下翻飞,油星四溅,全然不顾那简单的衣装被污染。如此往复,明天还是如此。
高考之前有个预考的环节,有稳得资格者,也有大意失荆州者。获得当年高考资格的,继续苦读,没有获得者则一分为二,对自己水平如何早已心知肚明者坦然接受,或复读或就此偃旗息鼓,心中早有决定,而有失水准者则捶胸跺足,指天誓言,来年再战!据说复读最久者有八年甚至十年之多,终于金榜题名,可见“恒心”二字确是真实不虚。
进入七月,高考的日子渐行渐近。这个时候,有些同学可能也在想着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便三三两两地到菜市场买了几个西红柿、几根葱等等,在最后的高中学习日子给自己象征性地增加一点营养,或者最后一次到房东那里“借”点浆水,做一顿酸酸的浆水面,然后去参加高考。
大多数同学还是与平时一样,依然把土豆炒洋芋、自管自的协奏曲进行到底。那时候极少有家里人特意来陪考,甚至只有当看到孩子拎着小铝锅回来时,才知道高考结束了。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整个校园充斥着老师、同学们欢乐、上进、拚搏的氛围,大家以苦为乐,是真正的“家长苦供,老师苦教、学生苦学”,通渭学生的刻苦努力,一时传为佳话,自动自发的学风蔚然成风。
在大山环绕、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支撑的通渭,那个时候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也许就只有高考,由此也催生了一大批后来的成功者,走向更远的地方。无论如何,在通渭的学习经历,给每一位学子曾经留下过难以磨灭的印象,忆起那时的经历,虽苦犹甜!
值班编辑:看海 图片:网络 来源:清风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