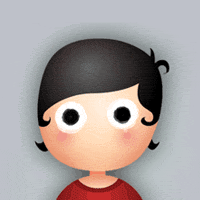盛夏酷暑,家家的餐桌上少不了一盘拌凉粉。那粉条洁白透明,如凝脂似琼玉。吃到嘴里凉爽滑溜,筋道可口。再佐以鲜红的水萝卜丝和碧绿的黄瓜丝,用辣椒油芝麻酱拌起来,真是色香味俱佳。这种凉粉是北方盛产的土豆淀粉做成的,快捷简便清热解暑。
尽管凉粉如此可口,但我总不忘河套农家别有风味的米凉粉它在我心中系着牢固的情结,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抹不掉。
在那经常搞“运动”的上世纪60年代初,。在当时的思想指导下,我们进村后工作很谨慎,纪律很严明,生怕误坐在“阶级敌人”的板凳上。自己戒备森严,神神秘秘;村民敬而远之,冷漠观望。上级要求我们必须周密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把“根”深深扎在真正的贫下中农中,必须坚持“三同”,即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同劳动”最好办,每天早早和社员出工,工作队员专拣重活脏活干就是了。“同吃最难解决,上级要求我们到最纯粹的贫下中农家吃“派饭”,千万别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谁是最纯粹的贫下中农呢?问村队干部吧,他们都是因为“四不清”被免职了。工作组长经过背靠背的调查摸底得知:全村共四十户人家,贫下中农成分的十四户,经过去粗取精,排除不纯粹的几户(条件是:贫下中农成分但是娶了不是贫农成分的儿媳妇者;贫下中农成分但是有小偷小摸或懒惰毛病者;贫下中农成分但是经常打架斗殴者。这些都没有资格接纳工作队的“派饭”),只剩下七户纯粹的。我们就在这几户轮流着吃派饭。
河套的农民非常憨厚热情,他们对工作队员敬如宾客。把能到其家派饭看作无尚的荣耀,情愿把家中最好的给我们吃,甚至割自己的肉都在所不惜。但工作队的纪律规定:不准吃鱼、肉、蛋。我们向这几家派饭户说明后,他们简直急眼了,说:“这哪能行?叫我们怎么做饭?河套人不种菜,只有鸡和猪,吃几个蛋还犯纪律?但纪律是铁的,我们只吃河套农家的家常便饭:中午白面馍,晚上麇子米酸捞饭。但他们尽量变着花样让我们吃好,馒头变烙油饼,烩酸菜里放肥猪肉,还说那是油不是肉。我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一斤粮票三角钱,吃完饭就结账。老白管钱和粮票。他是大机关搞财务的“头儿”,以他精于计算分毫的职业专长,自包自揽,声称:“我当你们的会计。”他背着一个那年头最讲究的军绿帆布书包,包带磨损得丝丝缕缕,包的颜色褪得灰不溜秋。我戏称它是“钱衩子”。
我们去张大娘家吃饭时,总看见她隔壁住的一个女人站在门口,目送我们进了张家,轻轻叹口气,甚至走到张家窗台前向屋里望望,眼神异样。我问张大娘,她是谁?大娘说:“是乔关老婆,她家也是贫农,你们没往她家派饭,她眼红我们呢!”
我一下和调查表格上的乔关家对上号。乔关是村里的赶胶车把式,给村里跑运输,经常外出不在家。他女人身体不好,常年有病,没有精力打理家务。有人就向工作组反映,她有懒惰的毛病。还有人说她和她男人经常半夜打架。的确是这样,工作组进村以来,乔关老婆经常半夜三更跑到工作组办公室告她丈夫的状,说她男人跑运输一回来就打她,她受不了了。老工作队员们听了就笑,说这两口子的事我们调解不了。乔关也不怕她告状,赶大车回来该怎样还怎样,稍不如意就拳脚相加。村里人也看不起她,她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可怜人。
吃过饭我从张家出来,乔关老婆又站在门口了,忙着和我们打招呼:“吃过了?”忍不住上前摸摸我的发辫,“喷喷,小李工作(组) 长着一头好头发,亮水水的。哎,老白工作,到我家坐坐吧!”我看清了她的长相,她是标准的河套农妇,生活贫困落后,饱经岁月风霜,没条件修饰自己。虽然才三十多岁,但是灰头土脸一副老态。时已暮春天气很热,她还穿着油渍麻花的灰布棉袄,脑门上罩一条脏得不颜色的头巾,松松垮垮挽在脑后,简直是个老太太。她身材瘦小,单薄孱弱,眼光无神。只有脸上白皙的肌肤,一对花眼皮河套人称“双眼皮”谓之),隐约显现她年轻时曾是个漂亮媳妇。
工作队开展了一阶段工作后,传来上面的文件精神,立即纠正以前过左的偏差,指出村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要团结大多数人,缩小打击面。工作组决定扩大派饭的范围,除了三户地主富农成分的和四户“四不清”干部家外,都能派饭了。工作组长让我通知这些户。我到了乔关家,说了些家常话,就告诉她正经事:“嫂子,明天来你家吃饭。”她好像没听到,愣怔地看着我,我又重复说了一次。她惊喜而诧异:“小李工作,你说啥,你们来我家吃饭?你可别要笑我。”“是真的,工作组要到你们家吃饭了!”她再无二话,掉过头双手捂着脸呜吗地哭开了。
第二天中午,我和老白等来到乔关家吃饭。走在路上我们开玩笑说,都说乔关老婆又懒又脏,家里乱得无从下脚,为了工作,我们意志坚强些,闭着眼睛吃吧!
那女人早早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开心地笑着,大声地招呼。她在油渍渍的灰棉袄外面罩了件夏天穿的白衬衫,腰身绷得鼓鼓的,没系头巾,头发用水梳得油光闪亮,两耳后各分出一缕头发,用花布条扎起来。显然是为了欢迎我们来吃饭,她特意打扮了一番她男人夜间回来了,听见声音也出来迎接我们。乔关魁梧身材,五大三粗,牛高马壮,望而生畏,黑黑的脸上堆着憨憨的笑。
她家的地和炕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所有的摆设——一只水缸和一个小柜擦得亮亮堂堂。我们坐下看到的却是冰锅冷灶,没有热气腾腾开饭的迹象。正在纳闷,乔关女人说:“饭早好了,你口气就吃。”转身进了院内小凉房,端进来一个大瓷盆,麻利地盛出三大碗,说:“快吃吧!咦,这是什么饭?乳黄色的半透明的筷子粗的长条,点着碧绿的葱花儿和鲜红的辣根。她热情洋溢地让着“快吃呀,这是米凉粉,我专门给你们工作人吃顿稀罕饭,这饭又解俄又解渴。”米一一凉—粉”,我第一次听到,第一次见到。一吃果然好吃得无法形容,光滑筋道,酸辣鲜美,清凉爽口,不用细嚼就下肚了,胃里涌起无限食欲,我们每人吃了两三碗。乔关老婆眼睛亮闪闪的,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问她,米怎么会变成凉粉,很费事吧?她说,不费事。乔关插话:“不费事?她昨夜就忙上了,作务了一黑夜,我第一次见她这样有精神。”乔关女人向我们介绍了米凉粉的作法:
先把糜子米闷得半生半熟晾凉,用擀面杖压碎,再用细萝筛滤去粗渣。然后把滤下的精细米糊放在锅内熬,待水分蒸发得差不多时,加一点儿榆树皮粉或者蒿籽面(为了增筋),就着热气用勺子向一个方向搅。越搅米糊粉就越上筋,听见爆发出叭叭的响声,就把它出锅摊在案板上或柜盖上。像泥瓦工用抹子抹墙一样,抹得匀匀的薄薄的。等晾凉后卷起来切成条,拌上各种佐料即可。
粗糙的糜米变成精细的米凉粉,这可是粗粮细做的经典啊!
这么复杂的工序,她竟说不费事,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
老白照例从包里掏出钱和粮票,他的表情很复杂,仿佛在沉思:乔关家的这顿饭这份情可是没法衡量的呀!那分明是她掏出的一颗热乎乎的心。
吃着这河套风味的米凉粉,我眼前闪现出乔关老婆欣喜辛劳的身影。我在香甜的滋味中悟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滋味……
作者:李敏,丰镇人,中共党员, 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1966年毕业,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休后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出版文集《河套情故乡情》。曾在多家网络平台、诗刊发表过诗词。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
阅读原文